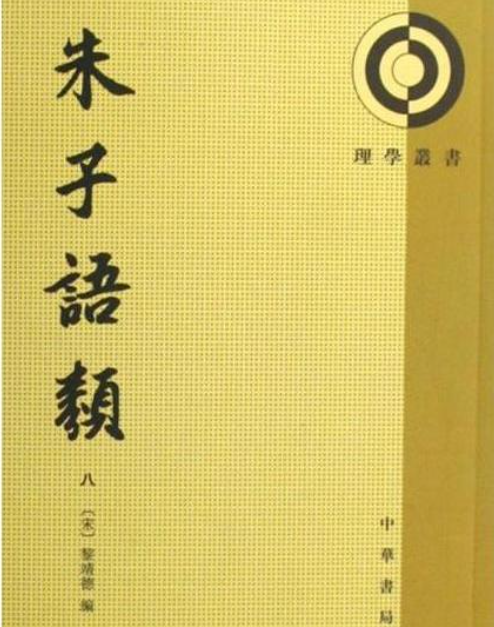诗二
周南关雎兼论二南。
诗未论音律,且如读二南,与郑卫之诗相去多少!
问:「程氏云:『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浅深言之?」曰:「不然。」问:「莫是王者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说,便可见。大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只看那『化』字与『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见二南犹乾坤也。」
「前辈谓二南犹易之乾坤,其诗粹然无非道理,与他诗不同。」曰:「须是宽中看紧底意思。」因言:「匡衡汉儒,几语亦自说得好。」曰:「便是他做处却不如此。」炎。
关雎一诗文理深奥,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读详味,不可说。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于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读诗须得他六义之体,如风雅颂则是诗人之格。后人说诗以为杂雅颂者,缘释七月之诗者以为备风雅颂三体,所以启后人之说如此。」又曰:「『兴』之为言,起也,言兴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兴物诗也。如『稿砧今何在』?『何当大刀头』皆是比诗体也。」
敬子说诗周南。曰:「他大纲领处只在戒慎恐惧上。只自『关关雎鸠』便从这里做起,后面只是渐渐推得阔。」
读关雎之诗,便使人有齐庄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与礼首言「毋不敬」,书首言「钦明文思」,皆同。
问:「二南之诗,真是以此风化天下否?」曰:「亦不须问是要风化天下与不风化天下,且要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云云里面看义理是如何。今人读书,只是说向外面去,却于本文全不识!」
「关雎之诗,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宫闱中所作。」问:「程子云是周公作。」曰:「也未见得是。」
关雎,看来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侧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天理、人欲。
说后妃多,失却文王了。今以「君子」为文王。伊川诗说多未是。
问器远:「君举所说诗,谓关雎如何?」曰:「谓后妃自谦,不敢当君子。谓如此之淑女,方可为君子之仇匹,这便是后妃之德。」曰:「这是郑氏也如此说了。某看来,恁地说也得。只是觉得偏主一事,无正大之意。关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无方际!如下面诸篇,却多就一事说。这只反复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说道甚么是德。只恁地浑沦说,这便见后妃德盛难言处。」
问曹兄云:「陈丈说关雎如何?」曹云:「言关雎以美夫人,有谦退不敢自当君子之德。」曰:「如此,则淑女又别是一个人也。」曹云:「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说经,多是恁地回互说去。如史丞相说书,多是如此。说『祖伊恐奔告于受』处,亦以纣为好人而不杀祖伊;若他人,则杀之矣。」先生乃云:「读书且虚心去看,未要自去取舍。且依古人书恁地读去,久后自然见得义理。」
魏兄问「左右芼之」。曰:「芼,是择也;左右择而取之也。」
解诗,如抱桥柱浴水一般,终是离脱不得鸟兽草木。今在眼前识得底,便可穷究。且如雎鸠,不知是个甚物?亦只得从他古说,道是「鸷而有别」之类。
魏才仲问:「诗关雎注:『挚,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说,似形容其美,何如?」曰:「也只是恁地。」问「芼」字。曰:「择也。读诗,只是将意思想象去看,不如他书字字要捉缚教定。诗意只是迭迭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关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当知君子之德如此;又当知诗人形容得意味深长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当知所以齐家,所以治国,所以平天下,人君则必当如文王,后妃则必当如太姒,其原如此。」
雎鸠,毛氏以为「挚而有别」。一家作「猛挚」说,谓雎鸠是鹗之属。鹗自是沉挚之物,恐无和乐之意。盖「挚」与「至」同,言其情意相与深至,而未尝狎,便见其乐而不淫之意。此是兴诗。兴,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鸠是挚而有别之物,荇菜是洁净和柔之物,引此起兴,犹不甚远。其它亦有全不相类,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虽皆是兴,与关雎又略不同也。
古说关雎为王雎,挚而有别,居水中,善捕鱼。说得来可畏,当是鹰鹯之类,做得勇武气象,恐后妃不然。某见人说,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虽两两相随,然相离每远,此说却与列女传所引义合。浩。
王鸠,尝见淮上人说,淮上有之,状如此间之鸠,差小而长,常是雌雄二个不相失。虽然二个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处,须是隔丈来地,所谓「挚而有别」也。「人未尝见其匹居而乘处。」乘处,谓四个同处也。只是二个相随,既不失其偶,又未尝近而相狎,所以为贵也。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虫,夜行于地。『熠耀』,言其光耳,非萤也。虬,今之苦[艹买]。」
卷耳
问:「卷耳与前篇葛覃同是赋体,又似略不同。盖葛覃直叙其所尝经历之事,卷耳则是托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设使不曾经历,而自言我之所怀者如此,则亦是赋体也。若螽斯则只是比,盖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孙众多。『宜尔子孙振振兮!』却自是说螽斯之子孙,不是说后妃之子孙也。盖比诗多不说破这意,然亦有说破者。此前数篇,赋、比、兴皆已备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时举因云:「螽,只是春秋所书之螽。窃疑『斯』字只是语辞,恐不可把『螽斯』为名。」曰:「诗中固有以『斯』为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类,是也。然七月诗乃云『斯螽动股』,则恐『螽斯』即便是名也。」
樛木
问:「樛木诗『乐只君子』,作后妃,亦无害否?」曰:「以文义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某所著诗传,盖皆推寻其脉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语,自是不泥着。」某云:「诗人道言语,皆发乎情,又不比他书。」曰:「然。」
螽斯
不妒忌,是后妃之一关雎所论是全体。
兔罝
问:「兔罝诗作赋看,得否?」曰:「亦可作赋看。但其辞上下相应,恐当为兴。然亦是兴之赋。」
汉广
问:「文王时,纣在河北,政化只行于江汉?」曰:「然。西方亦有玁狁。」
汉广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岂当时妇人蒙化,而男子则非!亦是偶有此样诗说得一边。
问:「『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兴,何如?」曰:「主意只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两句。六句是反复说。如『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兔,遇犬获之。』上下六句,亦只兴出『他人有心』两句。」诗传今作「兴而比」。
汝坟
君举诗言,汝坟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汉是闻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泽者。却有意思。
麟趾
问:「麟趾驺虞之诗,莫是当时有此二物出来否?」曰:「不是,只是取以为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驺虞。」又问:「诗序说『麟趾之时』,无义理。」曰:「此语有病。」
时举说:「『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似亦不成文理。」曰:「是。」
召南鹊巢
问:「召南之有鹊巢,犹周南之有关雎。关雎言『窈窕淑女』,则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鹊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鸠之为物,其性专静无比,可借以见夫人之德也。」
采蘩
问:「采苹蘩以供祭祀,采枲耳以备酒浆,后妃夫人恐未必亲为之。」曰:「诗人且是如此说。」
器之问:「采蘩何故存两说?」曰:「如今不见得果是如何,且与两存。从来说蘩所以生蚕,可以供蚕事。何必底死说道只为奉祭事,不为蚕事?」
问:「采蘩诗,若只作祭事说,自是晓然。若作蚕事说,虽与葛覃同类而恐实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妇职,以为同类,亦无不可,何必以蚕事而后同耶?」曰:「此说亦姑存之而已。」
殷其雷
问:「殷其雷,比君子于役之类,莫是宽缓和平,故入正风?」曰:「固然。但正、变风亦是后人如此分别,当时亦只是大约如此取之。圣人之言,在春秋易书无一字虚。至于诗,则发乎情,不同。」
摽有梅
问:「摽有梅何以入于正风?」曰:「此乃当文王与纣之世,方变恶入善,未可全责备。」
问:「摽有梅之诗固出于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尝见晋、宋闲有怨父母之诗。读诗者于此,亦欲达男女之情。」
江有汜
器之问江有汜序「勤而无怨」之说。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诗序自是两三人作。今但信诗不必信序。只看诗中说『不我以』,『不我过』,『不我与』,便自见得不与同去之意,安得『勤而无怨』之意?」因问器之:「此诗,召南诗。如何公方看周南,便又说召南?读书且要逐处沉潜,次第理会,不要班班剥剥,指东摘西,都不济事。若能沉潜专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养性之法。」
何彼秾矣
问:「何彼秾矣之诗,何以录于召南?」曰:「也是有些不稳当。但先儒相传如此说,也只得恁地就他说。如定要分个正经及变诗,也自难考据。如颂中尽多周公说话,而风雅又未知如何。」
「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只是一句,其语拙耳。
驺虞
驺虞之诗,盖于田猎之际,见动植之蕃庶,因以赞咏文王平昔仁泽之所及,而非指田猎之事为仁也。礼曰:「无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诗「彼茁者葭」,仁也;「一发五豝」,义也。
仁在一发之前。使庶类蕃殖者,仁也;「一发五豝」者,义也。
「于嗟乎驺虞!」看来只可解做兽名。以「于嗟麟兮」类之,可见。若解做驺虞官,终无甚意思。
邶柏舟
问:「『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注作比义。看来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亦无异,彼何以为兴?」曰:「他下面便说淑女,见得是因彼兴此。此诗纔说柏舟,下面更无贴意,见得其义是比。」
陈器之疑柏舟诗解「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太深。又屡辨赋、比、兴之体。曰:「赋、比、兴固不可以不辨。然读诗者须当讽味,看他诗人之意是在甚处。如柏舟,妇人不得于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又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其词气忠厚恻怛,怨而不过如此,所谓『止乎礼义』而中喜怒哀乐之节者。所以虽为变风,而继二南之后者以此。臣之不得于其君,子之不得于其父,弟之不得于其兄,朋友之不相信,处之皆当以此为法。如屈原不忍其愤,怀沙赴水,此贤者过之也。贾谊云:『历九州岛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则又失之远矣!读诗须合如此看。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诗中一个大义,不可不理会得也!」
器之问:「『静言思之,不能奋飞!』似犹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说,无过当处。既有可怨之事,亦须还他有怨底意思,终不成只如平时,却与土木相似!只看舜之号泣旻天,更有甚于此者。喜怒哀乐,但发之不过其则耳,亦岂可无?圣贤处忧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绿衣言『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绿衣
或问绿衣卒章「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为,恰与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后乎千百世之未来,只是此个道理。孟子所谓『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正谓是尔。」
燕燕
或问:「燕燕卒章,戴妫不以庄公之已死,而勉庄姜以思之,可见温和惠顺而能终也。亦缘他之心塞实渊深,所禀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词气温和,义理精密如此!秦汉以后无此等语。某读诗,于此数句;读书,至『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深诵叹之!」
时举说:「燕燕诗前三章,但见庄姜拳拳于戴妫,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见庄姜于戴妫非是情爱之私,由其有塞渊温惠之德,能自淑慎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己以不忘,则见戴妫平日于庄姜相劝勉以善者多矣。故于其归而爱之若此,无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颔之。
日月终风
又说:「日月终风二篇,据集注云,当在燕燕之前。以某观之,终风当在先,日月当次之,燕燕是庄公死后之诗,当居最后。盖详终风之辞,庄公于庄姜犹有往来之时,但不暴则狎,庄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则见庄公已绝不顾庄姜,而庄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观之,则终风当先,而日月当次。」曰:「恐或如此。」
式微
器之问:「式微诗以为劝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随它当时所作之意如此,便与存在,也可以见得有羁旅狼狈之君如此,而方伯连帅无救恤之意。今人多被『止乎礼义』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说。且要平心看诗人之意。如北门只是说官卑禄薄,无可如何。又如摽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来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向见伯恭丽泽诗,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诗,亦自鄙俚可恶。后来思之,亦自是见得人之情处。为父母者能于是而察之,则必使之及时矣,此所谓『诗可以观』。」子升问:「丽泽诗编得如何?」曰:「大纲亦好,但自据他之意拣择。大率多喜深巧有意者,若平淡底诗,则多不取。」问:「此亦有接续三百篇之意否?」曰:「不知。他亦须有此意。」
简兮
问:「简兮诗,张子谓『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过人者』。夫能卷而怀之,是固可以为贤。然以圣贤出处律之,恐未可以为尽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贱;其所执者,犹是先王之正乐。故献工之礼,亦与之交酢。但贤者而为此,则自不得志耳。」
泉水
问:「『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注云:『安得出游于彼,而写其忧哉!』恐只是因思归不得,故欲出游于国,以写其忧否?」曰:「夫人之游,亦不可轻出,只是思游于彼地耳。」
北门
问:「北门诗,只作赋说,如何?」曰:「当作赋而比。当时必因出北门而后作此诗,亦有比意思。」
问:「『莫赤匪狐,莫黑匪乌』,狐与乌,不知诗人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当国将危乱时,凡所见者无非不好底景象也。」
静女
问:「静女,注以为淫奔期会之诗,以静为闲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与狎溺,又何取乎闲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为可丑,但见其为可爱耳。以女而俟人于城隅,安得谓之闲雅?而此曰『静女』者,犹日月诗所谓『德音无良』也。无良,则不足以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爱之之辞也。」
二子乘舟
问:「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语,谓二子与申生不明骊姬之过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扬,谓三人皆恶伤父之志,而终于死之,其情则可取。虽于理为未当,然视夫父子相杀,兄弟相戮者,则大相远矣!」
因说,宣姜生卫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卫伋寿。以此观之,则人生自有秉彝,不系气类。
干旄
问文蔚:「『彼姝者子』,指谁而言?」文蔚曰:「集传言大夫乘此车马,以见贤者。贤者言:『车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将何以告之?』」曰:「此依旧是用小序说。」「此只是傍人见此人有好善之诚。」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盖指贤者而言也。如此说,方不费力。今若如集传说,是说断了再起,觉得费力。」
淇奥
文蔚曰:「淇奥一篇,卫武公进德成德之序,始终可见。一章言切磋琢磨,则学问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仪服饰之盛,有诸中有形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锡圭璧则锻炼以精,温纯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亻间]、赫、咺』之词,三章但言『宽、绰、戏、谑』而已。于此可见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礼之意。」曰:「说得甚善。卫武公学问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岁,犹命群臣使进规谏。至如抑诗是他自警之诗,后人不知,遂以为戒厉王。毕竟周之卿士去圣人近,气象自是不同。且如刘康公谓『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说得这般言语出。」
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先生不作淫乱说,何如?」曰:「有个『君子于役』,如何别将这个做一样说?『由房』,只是人出入处。古人屋,于房处前有壁,后无壁,所以通内。所谓『焉得谖草,言树之背』,盖房之北也。」
狡童兼论郑诗。
郑卫皆淫奔之诗,风雨狡童皆是。又岂是思君子,刺忽?忽愚,何以为狡?
经书都被人说坏了,前后相仍不觉。且如狡童诗是序之妄。安得当时人民敢指其君为「狡童」!况忽之所为,可谓之愚,何狡之有?当是男女相怨之诗。浩。
问:「『狡童,刺忽也。』古注谓诗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辈尝举春秋书忽之法,且引硕鼠以况其义。先生诗解取程子之言,谓作诗未必皆圣贤,则其言岂免小疵?孔子删诗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为后戒耳。琮谓,郑之诗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应删去。」曰:「如何见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谓『彼』者,它人之义也;所谓『子』者,尔之义也。他与尔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诗人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为忧忽之辞,则『彼狡童兮』,自应别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谁?」曰:「必是当时擅命之臣。」曰:「『不与我言兮』,却是如何?」曰:「如祭仲卖国受盟之事,国人何尝与知?琮因是以求硕鼠之义,乌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经,尽是诗序误人。郑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会托婚大国,而借其助矣。谓之顽童可也。许多郑风,只是孔子一言断了曰:『郑声淫。』如将仲子,自是男女相与之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辞,却干忽与突争国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见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郑风,诗序大率皆然。」问:「每篇诗名下一句恐不可无,自一句而下却似无用。」曰:「苏氏有此说。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台,如何是乐得贤?甚至汉广之诗,宁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德广所及也』一句成甚说话!」又问:「大序如何?」曰:「其间亦自有凿说处,如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礼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其职不过掌书,无掌诗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国史甚事?」曰:「旧闻先生不取诗序之说,未能领受。今听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诗!」琮。
江畴问:「『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当时之暴敛于民观之,为言亦不为重。盖民之于君,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雠。如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是也。然诗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诗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说。圣人言『郑声淫』者,盖郑人之诗,多是言当时风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语。狡童,想说当时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诗辞多是出于当时乡谈鄙俚之语,杂而为之。如鸱鸮云『拮据』、『捋荼』之语,皆此类也。」又曰:「此言乃周公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聱牙难考。如书中周公之言便难读,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无逸一书,中间用字亦有『诪张为幻』之语。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样文字,必出于当时有司润色之文,非纯周公语也。」又曰:「古人作诗,多有用意不相连续。如『嘒彼小星,三五在东』,释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东』者,是五纬之星应在于东也。其言全不相贯。」
问:「硕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硕鼠刺君重敛,盖暴取虐民,民怨之极,则将视君如寇仇,故发为怨上之辞至此。若狡童诗,本非是刺忽。纔做刺忽,便费得无限杜撰说话。郑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这般人,大言无当,有甚狡处?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郑突却是狡。诗意本不如此。圣人云:『郑声淫。』盖周衰,惟郑国最为淫俗,故诸诗多是此事。东莱将郑忽深文诋斥得可畏。」
曹云:「陈先生以此诗不是刺忽,但诗人说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微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狡童不与我言,则已之。」曰:「又去里面添一个『休』字也。这只是卫人当时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为君言也。」
鸡鸣
问:「鸡鸣诗序却似不妨,诗中却要理会。其曰:『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旧注谓夫人以蝇声为鸡声,所以警戒。所恃以感君听者,言有诚实而已。今鸡本未鸣,乃借蝇声以绐之,一夕偶然,其君尚以为非信,它夕其复敢言乎?」「是。」曰:「莫是要作推托不肯起之意在否?鄙见政谓是酬答之辞。」曰:「如此说,亦可。」琮。
着
问:「着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觉是亲迎底诗。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说何人亲迎。所说『尚之以青、黄、素、琼、瑶、瑛』,大抵只是押韵。如卫诗说『良马六』,此是天子礼,卫安得而有之!看来只是押韵。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于耳中,为复是塞在耳外?看来恐只是以线穿垂在当耳处。」
甫田
子善问:「甫田诗『志大心劳』。」曰:「小序说『志大心劳』,已是说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进,求之以道,则志不为徒大,心亦何劳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远大。然下手做时,也须一步敛一步,着实做始得。若徒然心务高远,而不下着实之功,亦何益哉!」
「骄骄」,张王之意,犹曰畅茂桀敖耳。「桀桀」与「骄骄」之义同,今田亩间莠最硬抢。
园有桃
园有桃,似比诗。
蟋蟀
问:「如蟋蟀之序,全然凿说,固不待言。然诗作于晋,而风系于唐,却须有说。」曰:「本是唐,及居晋水,方改号晋。」琮曰:「莫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无晋否?」曰:「文侯之命,书序固称『晋』矣。」曰:「书序想是纪事之词。若如春秋书『晋』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后,岂亦系诗之意乎?」曰:「恁地说忒紧,恰似举子做时文去。」琮。
蟋蟀自做起底诗,山有枢自做到底诗,皆人所自作。
豳七月
问:「豳诗本风,而周礼钥章氏祈年于田祖,则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则吹豳颂。不知就豳诗观之,其孰为雅?孰为颂?」曰:「先儒因此说,而谓风中自有雅,自有颂,虽程子亦谓然,似都坏了诗之六义。然有三说:一说谓豳之诗,吹之,其调可以为风,可为雅,可为颂;一说谓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载芟丰年诸篇是豳之颂,谓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则谓豳之诗自有雅颂,今皆亡矣。数说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问:「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为首,则谓之正月?抑只谓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诗之月数,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间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国语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为改月,则与孟子春秋相合,而与诗书不相合。若以为不改月,则与诗书相合,而与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问:「东莱曰:『十月而曰「改岁」,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举而迭用之耳。』据诗,如『七月流火』之类,是用夏正;『一之日觱发』之类,是周正;即不见其用商正。而吕氏以为『举而迭用之』,何也?」曰:「周历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时,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国僻远,无纯臣之义,又自有私纪其时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无纯臣」语,恐记误。
问:「『跻彼公堂,称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国小,君民相亲,其礼乐法制未必尽备。而民事之艰难,君则尽得以知之。成王时礼乐备,法制立,然但知为君之尊,而未必知为国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诗,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鸱鸮
因论鸱鸮诗,问:「周公使管叔监殷,岂非以爱兄之心胜,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说不敢疑,则已是有可疑者矣。盖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体,今既克商,使之监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无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异,造出一件事,周公为之柰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谓『周公之过,不亦宜乎』者,正谓此也。」曰:「然。」
或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解者以为武庚既杀我管蔡,不可复乱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毕竟当初是管蔡挟武庚为乱。武庚是纣子,岂有父为人所杀,而其子安然视之不报雠者?」曰:「诗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归怨管蔡。周公爱兄,只得如此说,自是人情是如此。不知当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监他,做出一场大疏脱?合天下之力以诛纣了,却使出屋里人自做出这一场大疏脱!这是周公之过,无可疑者。然当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见那时好在,必不疑他。后来有这样事,管蔡必是被武庚与商之顽民每日将酒去灌啖它,乘醉以语言离间之曰:『你是兄,却出来在此;周公是弟,反执大权以临天下!』管蔡呆,想被这几个唆动了,所以流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这都是武庚与商之顽民教他,使得管蔡如此。后来周公所以做酒诰,丁宁如此,必是当日因酒做出许多事。其中间想煞有说话,而今书、传只载得大概,其中更有几多机变曲折在。」
东山
问:「东山诗序,前后都是,只中间插『大夫美之』一句,便知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一手,是后人旋旋添续,往往失了前人本意,如此类者多矣。」
诗曲尽人情。方其盛时,则作之于上,东山是也;及其衰世,则作之于下,伯兮是也。
破斧
破斧诗,看圣人这般心下,诗人直是形容得出!这是答东山之诗。古人做事,苟利国家,虽杀身为之而不辞。如今人个个计较利害,看你四国如何不安也得,不宁也得,只是护了我斨、我斧,莫得阙坏了。此诗说出极分明。毛注却云四国是管蔡商奄。诗里多少处说「四国」,如正是「四国」之类,犹言四海。他却不照这例,自恁地说。
破斧诗,须看那「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见得周公用心始得。这个却是个好话头。
问:「破斧诗传何以谓『被坚执锐皆圣人之徒』?」曰:「不是圣人之徒,便是盗贼之徒。此语大概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带骨看,不成说圣人之徒便是圣人。且如『孳孳为善』是舜之徒,然『孳孳为善』亦有多少浅深。」义刚录详,别出。
安卿问:「破斧诗传云:『被坚执锐,皆圣人之徒。』似未可谓圣人之徒。」曰:「不是圣人之徒时,便是贼徒。公多年不相见,意此来必有大题目可商量,今却恁地,如何做得工夫恁地细碎!」安卿因呈问目。先生曰:「程子言:『有读了后全然无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者。』到这一二句喜处,便是入头处。如此读将去,将久自解踏着他关捩了,倏然悟时,圣贤格言自是句句好。须知道那一句有契于心,着实理会得那一句透。如此推来推去,方解有得。今只恁地包罩说道好。如吃物事相似,事事道好,若问那般较好,其好是如何,却又不知。如此,济得甚事?」因云:「如破斧诗,却是一个好话头,而今却只去理会那『圣人之徒』,便是不晓。」
先生谓淳曰:「公当初说破斧诗,某不合截得紧了,不知更有甚疑?」曰:「当初只是疑被坚执锐是粗人,如何谓之『圣人之徒』?」曰:「有粗底圣人之徒,亦有读书识文理底盗贼之徒。」
「破斧诗最是个好题目,大有好理会处,安卿适来只说那一句没紧要底。」淳曰:「此诗见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碍了。」曰:「只泥一句,便是未见得他意味。」
九罭
宽厚温柔,诗教也。若如今人说九罭之诗乃责其君之辞,何处讨宽厚温柔之意!
九罭诗分明是东人愿其东,故致愿留之意。公归岂无所?于汝但暂寓信宿耳。公归将不复来,于汝但暂寓信处耳。「是以有羇衣兮」,「是以」两字如今都不说。盖本谓缘公暂至于此,是以此间有被羇衣之人。「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其为东人愿留之诗,岂不甚明白?止缘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后之说诗者,悉委曲附会之,费多少辞语,到底鹘突!某尝谓死后千百年须有人知此意。自看来,直是尽得圣人之心!
「鸿飞遵渚,公归无所」;「鸿飞遵陆,公归不复」。「飞」、「归」协,是句腰亦用韵。诗中亦有此体。
狼跋
「狼跋其胡,载疐其尾」,此兴是反说,亦有些意义,略似程子之说。但程子说得深,如云狼性贪之类。「公孙硕肤」,如言「幸虏营」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毁,非四国之流言,乃公自逊此大美尔,此古人善于辞命处。
问:「『公孙硕肤』,注以为此乃诗人之意,言『此非四国之所为,乃公自让其大美而不居耳。盖不使谗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圣。此可见其爱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来诗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大伤巧得来不好。」曰:「自是作诗之体当如此,诗人只得如此说。如春秋『公孙于齐』,不成说昭公出奔!圣人也只得如此书,自是体当如此。」
问:「『公孙硕肤』,集传之说如何?」曰:「鲁昭公明是为季氏所逐,春秋却书云『公孙于齐』,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
二雅
小雅恐是燕礼用之,大雅须飨礼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间,大雅则止人君可歌。
大雅气象宏阔。小雅虽各指一事,说得精切至到。尝见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将作重事。近尝令孙子诵之,则见其诗果是恳如鹿鸣之诗,见得宾主之间相好之诚;如「德音孔昭」,「以燕乐嘉宾之心」,情意恳切,而不失义理之正。四牡之诗古注云:「无公义,非忠臣也;无私情,非孝子也。」此语甚切当。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将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说得恳切。如皇皇者华,即首云「每怀靡及」,其后便须「咨询」,「咨谋」。看此诗不用小序,意义自然明白。
鹿鸣诸篇
问:「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诗,仪礼皆以为上下通用之乐。不知为君劳使臣,谓『王事靡盬』之类,庶人安得而用之?」曰:「乡饮酒亦用。而『大学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谓习此。盖入学之始,须教他便知有君臣之义,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乐,小雅如鹿鸣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鱼鱼丽南山有台三篇;风则是关雎卷耳采蘩采苹等篇,皆是。然不知当初何故独取此数篇也。」
常棣
「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实以兄弟为不如友生也。犹言丧乱既平之后,乃谓反不如友生乎?盖疑而问之辞也。
苏宜又问:「常棣诗,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难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阋,犹能外御其侮,一节轻一节,而其所以着夫兄弟之义者愈重。到得丧乱既平,便谓兄弟不如友生,其『于所厚者薄』如此,则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乐时良心发处指出,谓酒食备而兄弟有不具,则无以共其乐;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则无以久其乐。盖居患难则人情不期而相亲,故天理常易复;处逸乐则多为物欲所转移,故天理常隐而难寻。所以诗之卒章有『是究是图,亶其然乎』之句。反复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二章,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须是恁地看。」
圣人之言,自是精粗轻重得宜。吕伯恭常棣诗章说:「圣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后不相悖。」此句说得极好!
伐木
问:「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发之也。」曰:「然。」又问:「『酾酒』,云『缩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乃以酹。」曰:「某亦尝疑今人用茅缩酒,古人刍狗乃酹酒之物。则茅之缩酒,乃今以醡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绢帛,故以茅缩酒也。」
问「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曰:「若能尽其道于朋友,虽鬼神亦必听之相之,而锡之以和平之福。」
天保
「何福不除」,义如「除戎器」之「除」。
问:「『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承是继承相接续之谓,如何?」曰:「松柏非是叶不凋,但旧叶凋时,新叶已生。木犀亦然。」
问:「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锡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锡尔以福;五章言民亦『遍为尔德』,则福莫大于此矣。故卒章毕言之。」曰:「然。」
时举说:「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颂祝其君之言。然辞繁而不杀者,以其爱君之心无已也。至四章则以祭祀先公为言;五章则以『遍为尔德』为言。盖谓人君之德必上无媿于祖考,下无媿于斯民,然后福禄愈远而愈新也。故末章终之以『无不尔或承』。」先生颔之。叔重因云:「蓼萧诗云『令德寿岂』,亦是此意。盖人君必有此德,而后可以称是福也。」曰:「然。」
采薇
又说:「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盖以玁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宁处;二章则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则竭力致死而无还心,不复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则惟勉于王事,而欲成其战伐之功也;卒章则言其事成之后,极陈其劳苦忧伤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诗,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极可玩味。风则或出于妇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观其大略耳。」
出车
问:「先生诗传旧取此诗与关雎诗,论『非天下之至静,不足以配天下之至健』处,今皆削之,岂亦以其太精巧耶?」曰:「正为后来看得如此,故削去。」曰:「关雎诗今引匡衡说甚好。」曰:「吕氏亦引,但不如此详。便见古人看文字,亦宽博如此。」
子善问:「诗『畏此简书』。简书,有二说:一说,简书,戒命也;邻国有急,则以简书相戒命。一说,策命临遣之词。」曰:「后说为长,当以后说载前。前说只据左氏『简书,同恶相恤之谓』。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谓之邻国也。」又问:「『胡不旆旆』,东莱以为初出军时,旌旗未展,为卷而建之,引左氏「建而不旆」。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飞扬乎?盖以命下之初,我方忧心悄悄,而仆夫憔悴,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说虽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语势似不如此。『胡不』,犹言『遐不作人』!言岂不旆旆乎!但我自『忧心悄悄』,而仆夫又况瘁耳,如此却自平正。伯恭诗太巧,诗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宽平,何尝如此纤细拘迫!」
鱼丽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这四句尽说得好。
南有嘉鱼
子善问南有嘉鱼诗中「汕汕」字。曰:「是以木叶捕鱼,今所谓『鱼花园』是也。」问枸。曰:「是机枸子,建阳谓之『皆拱子』,俗谓之『癞汉指头』,味甘而解酒毒。有人家酒房一柱是此木,而酝酒不成。左右前后有此,则亦酝酒不成。」
蓼萧
时举说蓼萧湛露二诗。曰:「文义也只如此。却更须要讽咏,实见他至诚和乐之意,乃好。」
六月
六月诗「既成我服」,不失机。「于三十里」。常度纪律。
采虬
时举说采虬诗。曰:「宣王南征蛮荆,想不甚费力,不曾大段战斗,故只极称其军容之盛而已。」
车攻
时举说车攻吉日二诗。先生曰:「好田猎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见得其车马之盛,纪律之严,所以为中兴之势者在此。其所谓田,异乎寻常之田矣。」
庭燎
时举说「庭燎有辉」。曰:「辉,火气也,天欲明而见其烟光相杂。此是吴才老之说,说此一字极有功也。」
斯干
扬问:「横渠说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学』,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学不好处。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岂可学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为兄者?但当尽其友可也。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为弟者岂可亦学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为弟者但当知其尽恭而已。如寇莱公挞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谓他底既不是,则不可学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诗之本意,『犹』字作相图谋说。」
「载弄之瓦。」瓦,纺砖也,纺时所用之物。旧见人画列女传,漆室乃手执一物,如今银子样。意其为纺砖也,然未可必。
节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它自窃国柄;少间又自不柰何,引得别人来,一齐不好了。如尹氏太师,只是它一个不好;少间到那「姻娅」处,是几个人不好了。
「『秉国之均。』均,本当从『金』,所谓如泥之在钧者,不知钧是何物。」时举曰:「恐只是为瓦器者,所谓『车盘』是也。盖运得愈急,则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钧。」曰:「『秉国之钧』,只是此义。今集传训『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运也。」
小弁
问:「小弁诗,古今说者皆以为此诗之意,与舜怨慕之意同。窃以为只『我罪伊何』一句,与舜『于我何哉』之意同。至后面『君子秉心,维其忍之』,与『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亲,却与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盖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说『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为无罪相似,未可与舜同日而语也。」问:「『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集传作赋体,是以上两句与下两句耶?」曰:「此只是赋。盖以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闻之也。」又曰:「看小雅虽未毕,且并看小雅后数篇大概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诗人所见极大,如巧言诗『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兔,遇犬获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恶巧言谗谮之人,却以『奕奕寝庙』与『秩秩大猷』起兴。盖以其大者兴其小者,便见其所见极大,形于言者,无非义理之极致也。」时举云:「此亦是先王之泽未泯,理义根于其心,故其形于言者,自无非义理。」先生颔之。
大东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诗传云:「兴也。」问:「似此等例,却全无义理。」曰:「兴有二义,有一样全无义理。」炎。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庚,续也。启明金星,长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将出则东见;水在日东,故日将没则西见。
楚茨
楚茨一诗,精深宏博,如何做得变雅!
问:「『神保是飨』,诗传谓神保是鬼神之嘉号,引楚辞语『思灵保兮贤姱』。但诗中既说『先祖是皇』,又说『神保是飨』,似语意重复,如何?」曰:「近见洪庆善说,灵保是巫。今诗中不说巫,当便是尸。却是向来解错了此两字。」
瞻彼洛矣
问:「瞻彼洛矣,洛水或云两处。」曰:「只是这一洛,有统言之,有说小地名。东西京共千里,东京六百里,西京四百里。」
问:「『韎韐有奭。』韎韐,毛郑以为祭服,王氏以为戎服。」曰:「只是戎服。左传云『有韎韦之跗注』,是也。」又曰:「诗多有酬酢应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归美其君,君子指君也。当时朝会于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华又是君报其臣,桑扈鸳鸯皆然。」
车牵
问:「列女传引诗『辰彼硕女』,作『展彼硕女』。」先生以为然,且云:「向来煞寻得。」
宾之初筵
或问:「宾之初筵诗是自作否?」曰:「有时亦是因饮酒之后作此自戒,也未可知。」
渐渐之石
周家初兴时,「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直恁地萧索!
大雅文王
大雅非圣贤不能为,其间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问:「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于天?只是人与天同。然观周自后稷以来,积仁累义,到此时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又问:「太王翦商,左氏云『太伯不从,是以不嗣』,莫是此意?」曰:「此事难明。但太王居于夷狄之邦,强大已久,商之政令,亦未必行于周。大要天下公器,所谓『有德者易以兴,无德者易以亡』。使纣无道,太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取,则是武王为乱臣贼子!若文王之事,则分明是盛德过人处。孔子于泰伯亦云『至德』。」
文王诗,直说出道理。
「帝命文王」,岂天谆谆然命之耶?只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如此,便是帝命之也。砺。
问:「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没,精神上与天合。看来圣人禀得清明纯粹之气,其生也既有以异于人,则其散也,其死与天为一;则其聚也,其精神上与天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别是一理,与众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个文王上上下下,则不可。若道诗人只胡乱恁地说,也不可。」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传「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之意。
马节之问「无遏尔躬」。曰:「无自遏绝于尔躬,如家自毁,国自伐。」
绵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动也;生,是兴起之意。当时一日之间,虞芮质成,而来归者四十余国,其势张盛,一时见之,如忽然跳起。又曰:「粗说时,如今人言军势益张。」
旧尝见横渠诗传中说,周至太王辟国已甚大,其所据有之地,皆是中国与夷狄夹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复见此书矣。意者,周之兴与元魏相似。初自极北起来,渐渐强大;到得后来中原无主,遂被他取了。
棫朴
问:「棫朴何以见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类如此。此篇与前后数诗,同为称扬之辞。作序者为见棫朴近个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苇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兴,何与人及草木?『以祈黄耇』是愿颂之词,如今人举酒称寿底言语。只见有『祈』字,便说是乞言。」
棫朴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来篇,皆是好诗,如何见得是伤今思古?只被乱在变雅中,便被后人如此想象。如东坡说某处猪肉,众客称美之意。
「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先生以为无甚义理之兴。或解云云。先生曰:「解书之法,只是不要添字。『追琢其章』者,以『金玉其相』故也;『勉勉我王』者,以『纲纪四方』故也。『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此是比得齐整好者也。」
诗无许多事。大雅精密。「遐」是「何」字。以汇推得之。又曰:「解诗,多是推类得之。」
「遐不作人」,古注并诸家皆作「远」字,甚无道理。礼记注训「胡」字,甚好。去伪录注云:「道随事着也。」
皇矣
周人咏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谓文王」言之,若曰,此盖天意云尔。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势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纣,故曰「至德」。
「时举说皇矣诗。先生谓此诗称文王德处,是从『无然畔援,无然歆羡』上说起;后面却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见得文王先有这个工夫,此心无一毫之私;故见于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圣人之私怒也。」问:「『无然畔援,无然歆羡』,窃恐是说文王生知之资,得于天之所命,自然无畔援歆羡之意。后面『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乃是文王做工夫处。」曰:「然。」
下武
「昭兹来许」,汉碑作「昭哉」。洪氏隶释「兹」、「哉」协韵。柏梁台诗末句韵亦同。
文王有声
问:「镐至丰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丰迁镐?」曰:「此只以后来事推之可见。秦始皇营朝宫渭南,史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故作之。想得迁镐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诸侯尽来朝觐,丰之故宫不足以容之尔。」
生民
生民诗是叙事诗,只得恁地。盖是叙,那首尾要尽,下武文王有声等诗,却有反复歌咏底意思。
问「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诗中有此语,自欧公不信祥瑞,故后人纔见说祥瑞,皆辟之。若如后世所谓祥瑞,固多伪妄。然岂可因后世之伪妄,而并真实者皆以为无乎?『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不成亦以为非!」
时举说「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处。曰:「『敏』字当为绝句。盖作母鄙反,协上韵耳。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诗中亦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盖以为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此等不可以言尽,当意会之可也。」
既醉
时举说既醉诗:「古人祝颂,多以寿考及子孙众多为言。如华封人祝尧:『愿圣人寿!愿圣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两事,孰有大于此者乎?」曰:「观行苇及既醉二诗,见古之人君尽其诚敬于祭祀之时,极其恩义于燕饮之际。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则其获福也宜矣,此所谓『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颔之。
子善问「厘尔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铢曰:「荆公作向后册云:『唯昔先王,厘厥士女。』『士女』与『女士』,义自不同。苏子由曾论及,曰:『恐它只是倒用了一字耳。』」因言荆公诰词中,唯此册做得极好,后人皆学之不能及。铢曰:「曾子固作皇太子册,亦放此。」曰:「子固诚是学它,只是不及耳。子固却是后面几个诰词好。国朝之制:外而三公三少,内而皇后太子贵妃皆有册。但外自三公而下,内自嫔妃而下,皆听其辞免。一辞即免。惟皇后太子用册。」
假乐
「千禄百福,子孙千亿!」是愿其子孙之众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是愿其子孙之贤。
舜功问:「『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是『勿忘、勿助长』之意?」曰:「不必如此说。不愆是不得过,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则能『率由旧章』。」
此诗末章则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纲」,而下章即继之曰「之纲之纪」。盖张之为纲,理之为纪。下面「百辟卿士」,至于庶民,皆是赖君以为纲。所谓「不解于位」者,盖欲纲常张而不弛也。
公刘
问:「第二章说『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时,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刘始于草创,而人从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问第四章「君之宗之」处。曰:「东莱以为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刘自为群君之君宗耳。盖此章言其一时燕飨,恐未说及立宗事也。」问「彻田为粮」处。先生以为「彻,通也」之说,乃是横渠说。然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则非民,私田不治则非吏」;似又与横渠之说不同,盖未必是计亩而分也。又问:「此诗与豳七月诗皆言公刘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来,至公刘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后,至于不窋,盖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不先不窋』。至于公刘乃始复修其业,故周室由是而兴也。」
时举说:「公刘诗『[革毕]琫容刀』,注云:『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谓[革毕]琫之中,容此刀也。」』如何谓之容臭?」曰:「如今香囊是也。」
卷阿
时举说卷阿诗毕,以为诗中凡称颂人君之寿考福禄者,必归于得人之盛。故既醉诗云:「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假乐诗言「受天之禄」,与「千禄百福」,而必曰「率由群匹」,与「百辟卿士,媚于天子」。盖人君所以致福禄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颔之。
民劳
时举窃谓,每章上四句是刺厉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铺叙如此,便自可见。故某以为古人非是直作一诗以刺其王,只陈其政事之失,自可以为戒。」时举因谓,第二章末谓:「无弃尔劳,以为王休」,盖以为王者之休,莫大于得人;惟群臣无弃其功,然后可以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后二句谓「敬慎威仪,以近有德」,盖以为既能拒绝小人,必须自反于己,又不可以不亲有德之人。不然,则虽欲绝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后二章「无俾正败」,「无俾正反」,尤见诗人忧虑之深。盖「正败」,则惟败坏吾之正道;而「正反」,则全然反乎正矣。其忧虑之意,盖一章切于一章也。先生颔之。
板
「『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旦与明祇一意。这个岂是人自如此?皆有来处。纔有些放肆,他便知。贺孙录云:「这里若有些违理,恰似天知得一般。」所以曰:『日监在兹。』」又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问:「『渝』字如何?」曰:「变也。如『迅雷风烈必变』之『变』,但未至怒。」贺孙录同。
道夫言:「昨来所论『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为人者,皆天之所为,故虽起居动作之顷,而所谓天者未尝不在也?」曰:「公说『天体物不遗』,既说得是;则所谓『仁体事而无不在』者,亦不过如此。今所以理会不透,祇是以天与仁为有二也。今须将圣贤言仁处,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见。记曰:『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钥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又曰:『宾入大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乐阕,孔子屡叹之。』」道夫曰:「如此,则是合正理而不紊其序,便是仁。」曰:「恁地猜,终是血脉不贯,且反复熟看。」
时举说板诗,问:「『天体物而不遗』,是指理而言;『仁体事而无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体事而无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发见尔。」因言:「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凡平日所讲贯穷究者,不知逐日常见得在吾心目间否?不然,则随文逐义,赶[走尔]期限,不见悦处,恐终无益。」余见张子书类。
荡
时举说:「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辞。后四句乃解前四句,谓天之降命,本无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终,故天命亦不克终,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纣之辞,而皆就人君身上说,使知其非天之如『女兴是力』,『尔德不明』,与『天不湎尔以酒』,『匪上帝不时』之类,皆自发明首章之意。」先生颔之。
抑
抑非刺厉王,只是自警。尝考卫武公生于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厉王之诗!据国语,只是自警。诗中辞气,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厉王,全然不顺。伯恭却谓国语非是。浩。
抑小序:「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不应一诗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且厉王无道,一旦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索休。且厉王监谤,暴虐无所不此诗无限大过,都不问着,却只点检威仪之末,此决不然!以史记考之,武公即位,在厉王死之后,宣王之时。说者谓是追刺,尤不是!伯恭主张小序,又云史记不可信,恐是武公必曾事厉王。若以为武公自警之诗,则其意味甚长。国语云,武公九十余岁作此诗。其间「匪我言耄」,可以为据。又如「谨尔侯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国之度,只是侯国之度耳。「曰丧厥国」,则是诸侯自谓无疑。盖武公作此诗,使人日夕讽诵以警己耳,所以有「小子」「告尔」之类,皆是箴戒作文之体自指耳。后汉侯芭亦有此说。
先生说:「抑诗煞好。」郑谓:「东莱硬要做刺厉王,缘以『尔』『汝』字碍。」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为叛;台中之评,人反以汝为倾等类,亦是自谓。古人此样多。大抵他说诗,其原生于不敢异先儒,将诗去就那序。被这些子碍,便转来穿凿胡说,更不向前来广大处去。或有两三说,则俱要存之。如一句或为兴,或为比,或为赋,则曰诗兼备此体。某谓既取兴体,则更不应又取比体;既取比体,则不更应又取赋体。说狡童,便引石虎事证,且要有字不曳白。南轩不解诗,道诗不用解,诸先生说好了。南轩却易晓,说与他便转。」
卫武公抑诗,自作懿戒也。中间有「呜呼小子」等语,自呼而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诗人美其「如切如磋」。
云汉
问:「云汉诗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责己处太少。」曰:「然。」
崧高
问:「崧高烝民二诗,是皆遣大臣出为诸侯筑城。」曰:「此也晓不得。封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诗,当初召伯带领许多车从人马去,也自劳攘。古人做事有不可晓者,如汉筑长安城,都是去别处调发人来,又只是数日便休。诗云:『溥彼韩城,燕师所完。』注家多说是燕安之众,某说即召公所封燕国之师。不知当初何故不只教本土人筑,又须去别处发人来,岂不大劳攘?古人重劳民,如此等事,又却不然,更不可晓,强说便成穿凿。」又曰:「看烝民诗,及左传国语周人说底话,多有好处。也是文武周公立学校,教养得许多人,所以传得这些言语,如烝民诗大故细腻。刘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说得好。」义刚录小异。
烝民
问:「烝民诗解云『仲山甫盖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则是为宰相可知。其曰『保兹天子』,『王躬是保』,则是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旧职。」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诗传中用东莱吕氏说。先生曰:「记得他甚主张那『柔』字。」文蔚曰:「他后一章云:『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刚柔不偏也。而二章首举『仲山甫之德』,独以『柔嘉维则』蔽之。崧高称『申伯番番』,终论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则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则干卦不用得了!人之资禀自有柔德胜者,自有刚德胜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郑公辈,是以刚德胜;如范忠宣范淳夫赵清献苏子容辈,是以柔德胜。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维则』,必要以此为入德之方,则不可。人之进德,须用刚健不息。」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谓『明哲』者,只是晓天下事理,顺理而行,自然灾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禄位。今人以邪心读诗,谓明哲是见几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扬子云说『明哲煌煌,旁烛无疆;逊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说话,所以它一生被这几句误。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义处,又不如此论。」
问:「『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处否?」曰:「安得此!只是见得道理分明,事事处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处,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杀身成仁处,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说中庸,无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见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见得理尽,便不可谓之明哲。学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无一事不当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将私看了,必至于孔光之徒而后已!」
周颂清庙
「假以溢我?」当从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转而为「假」也。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诗:「成王不敢康。」诗传皆断以为成王诗。某问:「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这个且只得做武王说。」炎。
我将
问:「我将乃祀文王于明堂之乐章。诗传以谓『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于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此乃周公以义起之,非古礼也』。不知周公以后,将以文王配耶?以时王之父配耶?」曰:「诸儒正持此二议,至今不决,看来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礼,不知在武王之时,在成王之时?若在成王,则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见。」又问:「继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
敬之
「日就月将」,是日成月长。就,成也;将,大也。
丝衣
绎,祭之明日也。宾尸,以宾客之礼燕为尸者。
鲁颂泮水
泮宫小序,诗传不取。或言诗中「既作泮宫」,则未必非修也。直卿云:「此落成之诗。」
閟宫
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是其事素定矣。横渠亦言周之于商,有不纯臣之义。盖自其祖宗迁豳,迁邰,皆其僻远自居,非商之所封土也。
商颂
商颂简奥。
伯丰问:「商颂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来王』等事!」又问:「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时所作,商尚质,不应商颂反多于周颂。」曰:「商颂虽多如周颂,觉得文势自别。周颂虽简,文自平易。商颂之辞,自是奥古,非宋襄可作。」又问:「颂是告于神明,却鲁颂中多是颂当时之君。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岂有此事?」曰:「是颂愿之辞。」又问:「『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孟子引以为周公,如何?」曰:「孟子引经自是不子细。」又问:「或谓鲁颂非三百篇之类,夫子姑附于此耳。」曰:「『思无邪』一句,正出鲁颂。」
玄鸟
问:「玄鸟诗吞卵事,亦有此否?」曰:「当时恁地说,必是有此。今不可以闻见不及,定其为必无。」
长发
「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天之生汤,恰好到合生时汤之修德,又无一日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