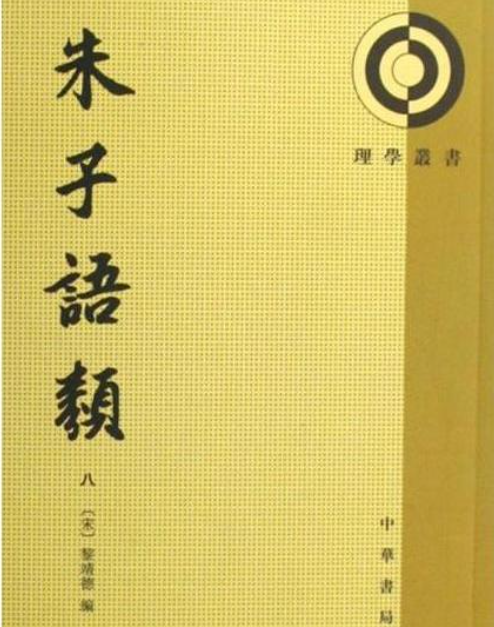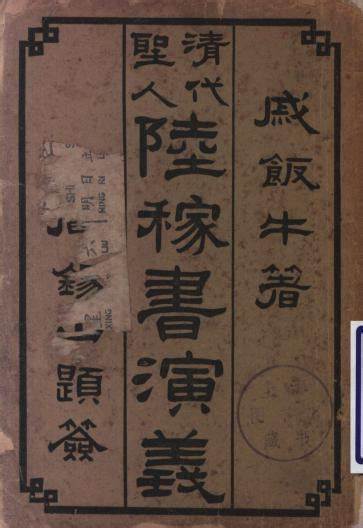尚书一
纲领
至之问:「书断自唐虞以下,须是孔子意?」曰:「也不可知。且如三皇之书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删去。五帝之书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删去。皆未可晓。」以下论三皇五帝。
陈仲蔚问:「『三皇』,所说甚多,当以何者为是?」曰:「无理会,且依孔安国之说。五峰以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却无高辛颛顼。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说。且如欧阳公说:『文王未尝称王』。不知『九年大统未集』,是自甚年数起。且如武王初伐纣之时,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又未知如何便称『王』?假谓史笔之记,何为未即位之前便书为『王』?且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书『殿前都点检』,安得便称『帝』耶!是皆不可晓。」又问:「欧公所作帝王世次序,辟史记之误,果是否?」曰:「是皆不可晓。昨日得巩仲至书,潘叔昌托讨世本。向时大人亦有此书,后因兵火失了,今亦少有人收得。史记又皆本此为之。且如孟子有滕定公,及世本所载,则有滕成公滕考公,又与孟子异,皆不可得而考。前人之误既不可考,则后人之论又以何为据耶!此事已厘革了,亦无理会处。」一本云:「问:『三皇当从何说?』曰:『只依孔安国之说。然五峰又将天地人作三皇,羲农黄唐虞作五帝,云是据易系说当如此。要之不必如此。且如欧公作泰誓论,言文王不称王,历破史迁之说。此亦未见得史迁全不是,欧公全是。盖泰誓有「惟九年大统未集」之说。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之说推之,不知九年当从何数起。又有「曾孙周王发」之说,到这里便是难理会,不若只两存之。又如世本所载帝王世系,但有滕考公成公,而无文公定公,此自与孟子不合。理会到此,便是难晓,亦不须枉费精神。』」
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如当时诰命出于史官,属辞须说得平易。若盘庚之类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当时曲折说话,所以难晓。以下论古、今文。
伏生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或者谓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错误,此不然。今古书传中所引书语,已皆如此,不可晓。」僩问:「如史记引周书『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类,此必非圣贤语。」曰:「此出于老子。疑当时自有一般书如此,故老子五千言皆缉缀其言,取其与己意合者则入之耳。」
问:「林少颖说,盘诰之类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盖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禹谟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方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又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今人作全书解,必不是。」
伯丰再问:「尚书古文、今文有优劣否?」曰:「孔壁之传,汉时却不传,只是司马迁曾师授。如伏生尚书,汉世却多传者,晁错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齐音不可晓者,以意属成,此载于史者。及观经传,及孟子引『享多仪』出自洛诰,却无差。只疑伏生偏记得难底,却不记得易底。然有一说可论难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书简说话,杂以方言,一时记录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盘诰之类是一时告语百姓;盘庚劝论百姓迁都之类,是出于记录。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属,或出当时做成底诏告文字,如后世朝廷词臣所为者。然更有脱简可疑处。苏氏传中于『乃洪大诰治』之下,略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纪考究得康诰非周公成王时,乃武王时。盖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语,若成王,则康叔为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称『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称『文王』。又有『寡兄』之语,亦是武王与康叔无疑,如今人称『劣兄』之类。又唐叔得禾,传记所载,成王先封唐叔,后封康叔,决无侄先叔之理。吴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后都称『王』,恐自是一篇。不应王告臣下,不称『朕』而自称『王』耳。兼酒诰亦是武王之时。如此,则是断简残编,不无遗漏。今亦无从考正,只得于言语句读中有不可晓者阙之。」又问:「壁中之书,不及伏生书否?」曰:「如大禹谟,又却明白条畅。虽然如此,其间大体义理固可推索。但于不可晓处阙之,而意义深远处,自当推究玩索之也。然亦疑孔壁中或只是畏秦焚坑之祸,故藏之壁间。大概皆不可考矣。」按家语后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藏尚书于孔子旧堂壁中。又汉史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
伯丰问「尚书未有解」。曰:「便是有费力处。其间用字亦有不可晓处。当时为伏生是济南人,晁错却颍川人,止得于其女口授,有不晓其言,以意属读。然而传记所引,却与尚书所载又无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晓,伏生所记者皆难晓。如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出于伏生,便有难晓处,如『载采采』之类。大禹谟便易晓。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难记?却记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晓。只牧誓中便难晓,如『五步、六步』之类。如大诰康诰,夹着微子之命。穆王之时,冏命君牙易晓,到吕刑亦难晓。因甚只记得难底,却不记得易底?便是未易理会。」
包显道举所看尚书数条。先生曰:「诸诰多是长句。如君奭『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违』是总说上天与民之意。汉艺文志注谓诰是晓谕民,若不速晓,则约束不行。便是诰辞如此,只是欲民易晓。」显道曰:「商书又却较分明。」曰:「商书亦只有数篇如此。盘依旧难晓。」曰:「盘却好。」曰:「不知怎生地,盘庚抵死要恁地迁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见大故为害。」曰:「他不复更说那事头。只是当时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属安于土而不肯迁,故说得如此。」曰:「大概伏生所传许多,皆聱牙难晓,分明底他又却不曾记得,不知怎生地。」显道问:「先儒将『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说,以为文王称王,不知有何据。」曰:「自太史公以来皆如此说了。但欧公力以为非,东坡亦有一说。但书说『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有这一个痕瑕。或推泰誓诸篇皆只称『文考』,至武成方称『王』,只是当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羁縻,那事体自是不同了。」
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某恐如盘庚周诰多方多士之类,是当时召之来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旅獒毕命微子之命君陈君牙冏命之属,则是当时修其词命,所以当时百姓都晓得者,有今时老师宿儒之所不晓。今人之所不晓者,未必不当时之人却识其词义也。
书有易晓者,恐是当时做底文字,或是曾经修饰润色来。其难晓者,恐只是当时说话。盖当时人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自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若使古人见今之俗语,却理会不得也。以其间头绪多,若去做文字时,说不尽,故只直记其言语而已。
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
典谟之书,恐是曾经史官润色来。如周诰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晓谕俗人者,方言俚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林少颖尝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万福』,使古人闻之,亦不知是何等说话。」
尚书中盘庚五诰之类,实是难晓。若要添减字硬说将去,尽得。然只是穿凿,终恐无益耳。
安卿问:「何缘无宣王书?」曰:「是当时偶然不曾载得。」又问:「康王何缘无诗?」曰:「某窃以『昊天有成命』之类,便是康王诗。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王业后,便不可晓。且如左传不明说作成王诗。后韦昭又且费尽气力,要解从那王业上去,不知怎生地!」
道夫请先生点尚书以幸后学。曰:「某今无工夫。」曰:「先生于书既无解,若更不点,则句读不分,后人承舛听讹,卒不足以见帝王之渊懿。」曰:「公岂可如此说?焉知后来无人!」道夫再三请之。曰:「书亦难点。如大诰语句甚长,今人却都碎读了,所以晓不得。某尝欲作书说,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属,祇以疏文为本。若其它未稳处,更与挑剔令分明,便得。」又曰:「书疏载『在璇玑玉衡』处,先说个天。今人读着,亦无甚紧要。以某观之,若看得此,则亦可以麤想象天之与日月星辰之运,进退疾迟之度皆有分数,而历数大概亦可知矣。」读尚书法。
或问读尚书。曰:「不如且读大学。若尚书,却只说治国平天下许多事较详。如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至『黎民于变』,这展开是多少!舜典又详。」
问致知读书之序。曰:「须先看大学。然六经亦皆难看,所谓:『圣人有郢书,后世多燕说』是也。知尚书收拾于残阙之余,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至穿凿。不若且看他分明处,其它难晓者姑阙之可也。程先生谓读书之法『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是也。且先看圣人大意,未须便以己意参之。如伊尹告太甲,便与傅说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谆切恳到,盖太甲资质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则无许多病痛,所谓『黩于祭祀,时谓弗钦』之类,不过此等小事尔。学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则如伊尹之言正用得着。盖有这般病,须是这般药。读圣贤书,皆要体之于己,每如此。」
问:「『尚书难读,盖无许大心胸。』他书亦须大心胸,方读得。如何程子只说尚书?」曰:「他书却有次第。且如大学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节次;尚书只合下便大。如尧典自:『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至『黎民于变时雍』,展开是大小大!分命四时成岁,便是心中包一个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见得恁地。若不得一个大底心胸,如何了得?」
某尝患尚书难读,后来先将文义分明者读之,聱讹者且未读。如二典三谟等篇,义理明白,句句是实理。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皋陶稷契伊傅辈所言所行,最好紬绎玩味,体贴向自家身上来,其味自别。
读尚书,只拣其中易晓底读。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此样虽未晓,亦不紧要。
「二典三谟其言奥雅,学者未遽晓会,后面盘诰等篇又难看。且如商书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说得极切。其所以治心修身处,虽为人主言,然初无贵贱之别,宜取细读,极好。今人不于此等处理会,却只理会小序。某看得书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然后人亦自理会他本义未得。且如『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说皋陶,后说禹,谓舜欲令禹重说,故将『申』字系『禹』字。盖伏生书以益稷合于皋陶谟,而『思曰赞赞襄哉』与『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连。『申之』二字,便见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说,说得虽多,皆非其本意也。」又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此是内外交相养法。事在外,义由内制;心在内,礼由外作。」铢问:「礼莫是摄心之规矩否?」曰:「礼只是这个礼,如颜子非礼勿视听言动之类,皆是也。」又曰:「今学者别无事,只要以心观众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观众理,只是此两事耳。」
问可学:「近读何书?」曰:「读尚书。」曰:「尚书如何看?」曰:「须要考历代之变。」曰:「世变难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汤誓,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大抵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着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诰太甲诸篇,只是熟读,义理自分明,何俟于解?如洪范则须着意解。如典谟诸篇,辞稍雅奥,亦须略解。若如盘庚诸篇已难解,而康诰之属,则已不可解矣。昔日伯恭相见,语之以此。渠云:『亦无可阙处。』因语之云:『若如此,则是读之未熟。』后二年相见,云;『诚如所说。』」
问:「读尚书,欲裒诸家说观之,如何?」先生历举王苏程陈林少颖李叔易十余家解讫,却云:「便将众说看未得。且读正文,见个意思了,方可如此将众说看。书中易晓处直易晓,其不可晓处,且阙之。如盘庚之类,非特不可晓,便晓了,亦要何用?如周诰诸篇,周公不过是说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当时说话,其间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观其大意所在而已。」又曰:「有功夫时,更宜观史。」
语德粹云:「尚书亦有难看者。如微子等篇,读至此,且认微子与父师、少师哀商之沦丧,己将如何。其它皆然。若其文义,知他当时言语如何,自有不能晓矣。」
书序恐不是孔安国做。汉文麤枝大叶,今书序细腻,只似六朝时文字。小序断不是孔子做!论孔序。
汉人文字也不唤做好,却是麤枝大叶。书序细弱,只是魏晋人文字。陈同父亦如此说。
「尚书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国所作。盖文字善困,不类西汉人文章,亦非后汉之文。」或言:「赵岐孟子序却自好。」曰:「文字絮,气闷人。东汉文章皆然。」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困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麤处,决不如此困善也。如书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卓。
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与毛公诗传大段不同。今观序文亦不类汉文章。汉时文字粗,魏晋间文字细。如孔丛子亦然,皆是那一时人所为。
孔安国尚书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汉文字甚次第。司马迁亦不曾从安国受尚书,不应有一文字软郎当地。后汉人作孔丛子者,好作伪书。然此序亦非后汉时文字,后汉文字亦好。
「孔氏书序不类汉文,似李陵答苏武书。」因问:「董仲舒三策文气亦弱,与晁贾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为人宽缓,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汉自武帝后,文字要入细,皆与汉初不同。」
「传之子孙,以贻后代。」汉时无这般文章。
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论孔传。
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于舜方止。今却说是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却说「历试诸艰」,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后诸篇皆然。况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
尚书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国作,怕只是撰孔丛子底人作。文字软善,西汉文字则麤大。论小序。
书小序亦非孔子作,与诗小序同。
书序是得书于屋壁,已有了,想是孔家人自做底。如孝经序乱道,那时也有了。
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人文字,只似后汉末人。又书亦多可疑者,如康诰酒诰二篇,必是武王时书。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称「寡兄」、「朕其弟」,却甚正。梓材一篇又不知何处录得来,此与他人言皆不领。尝与陈同甫言。陈曰:「每常读,亦不觉。今思之诚然。」
徐彦章问:「先生却除书序,不以冠篇首者,岂非有所疑于其间耶?」曰:「诚有可疑。且如康诰第述文王,不曾说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说武王,又是自称之词。然则康诰是武王诰康叔明矣。但缘其中有错说『周公初基』处,遂使序者以为成王时事,此岂可信?」徐曰:「然则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监之矣,又以何处封康叔?」曰:「既言『以殷余民封康叔』,岂非封武庚之外,将以封之乎?又曾见吴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后半截不是梓材,缘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词,未尝如前一截称『王曰』,又称『汝』,为上告下之词。亦自有理。」
或问:「书解谁者最好?莫是东坡书为上否?」曰:「然。」又问:「但若失之简。」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诸家解。
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学蒙。
东坡书解文义得处较多。尚有粘滞,是未尽透彻。
诸家注解,其说虽有乱道,若内只有一说是时,亦须还它底是。尚书句读,王介甫苏子瞻整顿得数处甚是,见得古注全然错。然旧看郭象解庄子,有不可晓处。后得吕吉甫解看,却有说得文义的当者。
因论书解,必大曰:「旧闻一士人说,注疏外,当看苏氏陈氏解。」曰:「介甫解亦不可不看。书中不可晓处,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从他说。但一段训诂如此说得通,至别一段如此训诂,便说不通,不知如何。」
「荆公不解洛诰,但云:『其间煞有不可强通处,今姑择其可晓者释之。』今人多说荆公穿凿,他却有如此处。若后来人解书,又却须要解尽。」
「易是荆公旧作,却自好。三经义诗书周礼。是后来作底,却不好。如书说『聪明文思』,便要牵就五事上说,此类不同。」铢因问:「世所传张纲书解,只是祖述荆公所说。或云是闽中林子和作,果否?」曰:「或者说如此,但其家子孙自认是它作。张纲后来作参政,不知自认与否?」子孙自认之说,当时失于再叩。后因见汪玉山驳张纲谥文定奏状,略云:「一,行状云:『公讲论经旨,尤精于书。着为论说,探微索隐,无一不与圣人契,世号张氏书解。』臣窃以王安石训识经义,穿凿傅会,专以济其刑名法术之说。如书义中所谓:『敢于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讫,凶德不可忌』之类,皆害理教,不可以训。纲作书解,掇拾安石绪余,敷衍而润饰之,今乃谓其言『无一不与圣人契』,此岂不厚诬圣人,疑误学者!」
先生因说,古人说话皆有源流,不是胡乱。荆公解「聪明文思」处,牵合洪范之五事,此却是穿凿。如小旻诗云「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却合洪范五事。此人往往曾传箕子之学。刘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语,亦是有所师承。不然,亦必曾见上世圣人之遗书。大抵成周时于王都建学,尽收得上世许多遗书,故其时人得以观览而剽闻其议论。当时诸国,想亦有书。若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鲁国书,犹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车马送至周,入王城,见老子,因得遍观上世帝王之书。
胡安定书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实之类不载。但言行录上有少许,不多,不见有全部。专破古说,似不是胡平日意。又间引东坡说。东坡不及见安定,必是伪书。
曾彦和,熙丰后人,解禹贡。林少颖吴才老甚取之。
林书尽有好处。但自洛诰已后,非他所解。
胡氏辟得吴才老解经,亦过当。才老于考究上极有功夫,只是义理上自是看得有不子细。其书解,徽州刻之。
李经叔易,伯纪丞相弟,解书甚好,亦善考证。
吕伯恭解书自洛诰始。某问之曰:「有解不去处否?」曰:「也无。」及数日后,谓某曰:「书也是有难说处,今只是强解将去尔。」要之,伯恭却是伤于巧。
向在鹅湖,见伯恭欲解书,云:「且自后面解起,今解至洛诰。」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闹热。某尝问伯恭:「书有难通处否?」伯恭初云:「亦无甚难通处。」数日问,却云:「果是有难通处。」
问:「书当如何看?」曰:「且看易晓处。其它不可晓者,不要强说;纵说得出,恐未必是当时本意。近世解书者甚众,往往皆是穿凿。如吕伯恭,亦未免此也。」
先生云:「曾见史丞相书否?」刘云:「见了。看他说『昔在』二字,其说甚乖。」曰:「亦有好处。」刘问:「好在甚处?」曰:「如『命公后』,众说皆云,命伯禽为周公之后。史云,成王既归,命周公在后。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见得是周公且在后之意。」
薛士龙书解,其学问多于地名上有功夫。
尧典
问:「序云:『聪明文思』,经作『钦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问:「恐是作序者见经中有『钦明文思』,遂改换『钦』字作『聪』字否?」曰:「然。」
「若稽古帝尧」,作书者叙起。
林少颖解「放勋」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说为优。
「安安」,只是个重迭字,言尧之「聪明文思」,皆本于自然,不出于勉强也。「允」,则是信实;「克」,则是能。
「安安」,若云止其所当止。上「安」字是用。下「安」字是体。「成性存存」亦然。又恐只是重字,若「小心翼翼」。「安安」、「存存」亦然。皆得。
「允恭克让」,从张纲说,谓「信恭能让」。作书者赞咏尧德如此。
「允恭克让」,程先生说得义理亦好,只恐书意不如此。程先生说多如此,诗尤甚,然却得许多义理在其中。
「格」,至也。「格于上下」,上至天,下至地也。
「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
「克明俊德」,只是说尧之德,与文王「克明德」同。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词意不是明俊德之士。
显道问:「尧典自『钦明文思』以下皆说尧之德。则所谓『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势,不见有用人意。」又问:「『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说者或谓大录万机之政,或谓登封太山,二说如何?」曰:「史记载『使舜入山林,烈风雷雨,弗迷其道』。当从史记。」
任道问:「尧典『以亲九族』,说者谓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林少颖谓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谓『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谓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谓母之本族,母族与姨母之家;妻族,则妻之本族,与其母族是也。上杀,下杀,旁杀,只看所画宗族图可见。」
「九族」,且从古注。「克明德」,是再提起尧德来说。「百姓」,或以为民,或以为百官族姓,亦不可考,姑存二说可也。「厘」则训治,「厘降」只是他经理二女下降时事尔。
「九族」,以三族言者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亲者皆是。「胤子朱」,做丹朱说,甚好。然古有胤国,尧所举,又不知是谁。鲧殛而禹为之用。圣人大公,无毫发之私。禹亦自知父罪当然。
「平章百姓」,只是近处百姓;「黎民」,则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谟中「百姓」,只是说民,如「罔咈百姓」之类。若是国语中说「百姓」,则多是指百官族姓。
「百姓」,畿内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齐而后国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纲五常皆分晓,不鹘突也。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内之民;「昭明」,只是与它分别善恶,辨是与非。以上下文言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
问:「孔传云:『百官族姓。』程子谓古无此说。吕刑只言『官伯族姓』。后有『百姓不亲』,『干百姓』,『咈百姓』,皆言民,岂可指为百官族姓?」「后汉书亦云部刺史职在『辨章百姓,宣美风俗』。辨章即平章也。」过又云:「族姓亦不可不明。」先生只曰:「未曾如此思量。」
尧舜之道,如「平章百姓」,「黎民于变时雍」之类,皆是。几时只是安坐而无所作为!履孙。
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
羲和主历象。授时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历是古时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鸟名官,首曰凤鸟氏,历正也。岁月日时既定,则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两说相兼,其义始备。
历是书,象是器。无历,则无以知三辰之所在:无玑衡,则无以见三辰之所在。
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类,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历耳。如唐时尚使人去四方观望。
问:「『寅宾出日』,『寅饯纳日』,如何?」曰:「恐当从林少颖解:『寅宾出日』,是推测日出时候;『寅饯纳日』,是推测日入时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旸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测日景之处。宅,度也。古书『度』字有作『宅』字者。『东作、南讹、西成、朔易』皆节候也。『东作』,如立春至雨水节之类。『寅宾』,则求之于日;『星鸟』,则求之于夜。『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后之事;夷者,万物收成,民皆优逸之意。『孳尾』至『氄毛』,亦是鸟兽自然如此,如今历书记鸣鸠拂羽等事。程泰之解旸谷南交昧谷幽都,以为筑一台而分为四处,非也。古注以为羲仲居治东方之官,非也。若如此,只是东方之民得东作,他处更不耕种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敛获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历之官,观于『咨汝羲暨和』之辞,可见。『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春、秋分无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长。」
「平秩东作」之类,只是如今谷雨、芒种之节候尔。林少颖作「万物作」之「作」说,即是此意。
「东作」,只是言万物皆作。当春之时,万物皆有发动之意,与「南讹、西成」为一类,非是令民耕作。羲仲一人,东方甚广,如何管得许多!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宾」是宾其出,「寅饯」是饯其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说者,北方无日故也。
「朔易」,亦是时候。岁亦改易于此,有终而复始之意。在,察也。
尧典云「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岁三百五十四日者,积朔空余分以为闰。朔空者,六小月也;余分者,五日四分度之一也。
自「畴咨若时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为禅位设也。一举而放齐举胤子,再举而驩兜举共工,三举而四岳举鲧,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伯恭说「子朱启明」之事不是。此乃为放齐翻款。尧问「畴咨若时登庸」?放齐不应举一个明于为恶之人。此只是放齐不知子朱之恶,失于荐扬耳。
包显道问:「朱先称『启明』,后又说他『嚚讼』,恐不相协?」曰:「便是放齐以白为黑,夔孙录云:「问:『「启明」与「嚚讼」相反。』『「静言庸违」则不能成功,却曰「方鸠僝功」,此便是驩兜以白为黑』云云。」以非为是,所以舜治他。但那人也是崎峣。且说而今暗昧底人,解与人健讼不解?惟其启明后,方解嚚讼。」又问:「尧既知鲧,如何尚用之?」曰:「鲧也是有才智,想见只是狠拗自是,所以弄得恁地郎当。所以楚辞说『鲧幸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处,坏了人多,弄八九年无收杀,故舜殛之。」夔孙录略。
共工驩兜,看得来其过恶甚于放齐、胤子朱。
「僝功」,亦非灼然知是为见功,亦且是依古注说。「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之类,都不成文理,不可晓。
「象恭滔天。」「滔天」二字羡,因下文而误。
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总十二牧者,百揆是总九官者。
问:「四岳是十二牧之长否?」曰:「周官言『内有百揆、四岳』,则百揆是朝廷官之长,四岳乃管领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为二十有二人,则四岳为一人矣。又,尧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尧欲以天下与四人也!又,周官一篇说三公、六卿甚分晓。汉儒如扬雄郑康成之徒,以至晋杜元凯,皆不曾见。直至东晋,此书方出。伏生书多说司马司空,乃是诸候三卿之制,故其诰诸侯多引此。顾命排列六卿甚整齐,太保奭冢宰。芮伯宗伯。彤伯司马。毕公司徒。卫侯司寇。毛公,司空。疏中言之甚详。康诰多言刑罚事,为司寇也。太保毕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职。三公本无职事,亦无官属,但以道义辅导天子而已。汉却以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失其制矣。」必大录别出。
正淳问「四岳、百揆」。曰:「四岳是总在外诸侯之官,百揆则总在内百官者。」又问:「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让与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见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书,汉武帝时方出,又不行于世,至东晋时方显,故扬雄赵岐杜预诸儒悉不曾见。如周官乃孔氏书,说得三公三孤六卿极分明。汉儒皆不知,只见伏生书多说司徒司马司空,遂以此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它篇说此三官者,皆是训诰诸侯之词。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书只顾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齐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召公与毕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卫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卫侯是康叔为司寇,所以康诰中多说刑。三公只是以道义傅保王者,无职事官属,却下行六卿事。」汉时太傅亦无官属。
「异哉」,是不用亦可。「试可乃已」,言试而可,则用之;亦可已而已之也。
尧知鲧不可用而尚用,此等事皆不可晓。当时治水事,甚不可晓。且如滔天之水满天下,如何用工!如一处有,一处无,尚可。既「洪水滔天」,不知如何掘地注海?今水深三尺,便不可下工。如水甚大,则流得几时,便自然成道,亦不用治。不知禹当时治水之事如何。
「庸命」、「方命」之「命」,皆谓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曰:「圆则行,方则止,犹今言废阁诏令也。」盖鲧之为人,悻戾自用,不听人言语,不受人教令也。
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后,在尧时不应在侧陋。此恐不然。若汉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孙,已在民间耕稼了。况上古人寿长,传数世后,经历之远,自然有微而在下者。
「烝烝」,东莱说亦好。曾氏是曾彦和。自有一本孙曾书解。孙是孙惩。
「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皆尧之言。「厘降二女于沩汭,嫔于虞」,乃史官之词。言尧以女下降于舜尔。「帝曰:『钦哉!』」是尧戒其二女之词,如所谓「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若如此说,不解亦自分明。但今解者便添入许多字了说。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此尧之言。「厘降二女于沩汭,嫔于虞。」此史官所记。厘,治也。「帝曰:『钦哉!』」尧之言。乃「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之意。「辑五瑞。」是方呼唤来。「乃日觐四岳、群牧」。随其到者,先后见之。「肆觐东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如五器。卒乃复。」文当次第如此。复,只是同。「象以典刑,是正刑:墨、劓、剕、宫、大辟。象,犹「县象魏」之「象」,画之令人知。流宥五刑,正刑有疑似及可悯者,随其重轻以流罪宥之。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鞭、扑,皆刑之小者。金作赎刑。鞭扑小刑之可悯者,令以金赎之。正刑则只是流,无赎法。眚梨肆赦。过误可悯,虽正刑亦赦。怙终贼刑。」怙终者,则贼刑。
「嫔于虞。帝曰:『钦哉!』」尧戒女也。
舜典
东莱谓舜典止载舜元年事,则是。若说此是作史之妙,则不然,焉知当时别无文字在?
「舜典自『虞舜侧微』至『乃命以位』,一本无之。直自尧典『帝曰钦哉』而下,接起『慎徽五典』,所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也。『玄德』难晓,书传中亦无言玄者。今人避讳,多以『玄』为『元』,甚非也。如『玄黄』之『玄』,本黑色。若云『元黄』,是『子畏于正』之类也。旧来颁降避讳,多以『玄』为『真』字,如『玄冥』作『真冥』,『玄武』作『真武』。」伯丰问:「既讳黄帝名,又讳圣祖名,如何?」曰:「旧以圣祖为人皇中之一,黄帝自是天降而生,非少昊之子。其说虚诞,盖难凭信也。」
「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细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浚,是明之发处;哲,则见于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着。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说;塞,是其中实处。
「『浚哲文明,温恭允塞』,是八德。」问:「『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纳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宾于四门』,是使之为行人之官;『纳大麓』,恐是为山虞之官。」曰:「若为山虞,则其职益卑。且合从史记说,使之入山,虽遇风雨弗迷其道也。」
「纳于大麓」,当以史记为据,谓如治水之类。「弗迷」,谓舜不迷于风雨也。若主祭之说,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迷?仍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风雷之变,岂得为好!
「烈风雷雨弗迷」,只当如太史公说。若从主祭说,则「弗迷」二字说不得。弗迷,乃指人而言也。
尧命舜曰:「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则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终于文祖」,只是摄行其事也。故舜之摄,不居其位,不称其号,只是摄行其职事尔。到得后来舜逊于禹,不复言位,止曰「总朕师」尔。其曰「汝终陟元后」,则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尔。
舜居摄时,不知称号谓何。观「受终」、「受命」,则是已将天下分付他了。
尧舜之庙虽不可考,然以义理推之,尧之庙当立于丹朱之国,所谓「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盖「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故礼记「有虞氏褅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伊川以为可疑。
书正义「璇玑玉衡」处,说天体极好。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注谓「察天文,审己当天心否」,未必然。只是从新整理起,此是最当先理会者,故从此理会去。
类,只是祭天之名,其义则不可晓。与所谓「旅上帝」同,皆不可晓,然决非是常祭。
问「六宗」。曰:「古注说得自好。郑氏『宗』读为『禜』,即祭法中所谓『祭时、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说,则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后遍及群神,次序皆顺。」问:「五峰取张髦昭穆之说,如何?」曰:「非唯用改易经文,兼之古者昭穆不尽称『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汉之庙,唯文帝称『太宗』,武帝称『世宗』,至唐朝乃尽称『宗』,此不可以为据。」
问:「『辑五瑞,既月,乃日观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恐只是王畿之诸侯;辑敛瑞玉,是命圭合信,如点检牌印之属。如何?」曰:「不当指杀王畿。如顾命,太保率东方诸侯,毕公率西方诸侯,不数日间,诸侯皆至,如此之速。」
汪季良问「望、禋」之说。曰:「注以『至于岱宗柴』为句。某谓当以『柴望秩于山川』为一句。」
「协时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时日月尔,非谓作历也。每遇巡狩,凡事理会一遍,如文字之类。
「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旧说皆云「如五器」,谓即是诸侯五玉之器。初既辑之,至此,礼既毕,乃复还之。看来似不如此,恐书之文颠倒了。五器,五礼之器也。五礼者,乃吉凶军宾嘉之五礼。凶礼之器,即是衰绖之类;军礼之器,即是兵戈之类;吉礼之器,即是簠簋之类。如者,亦同之义。言有以同之,使天下礼器皆归于一。其文当作「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如五器,卒乃复。」言诸侯既朝之后,方始同其律度量衡,修其五礼,如其五器,其事既卒而乃复还也。
问:「『修五礼』,吴才老以为只是五典之礼,唐虞时未有『吉凶军宾嘉』之名,至周时方有之,然否?」曰:「不然。五礼,只是吉凶军宾嘉,如何见得唐虞时无此?」因说:「舜典此段疑有错简。当云『肆觐东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如五器,卒乃复』。如者,齐一之义。『卒乃复』者,事毕复归也,非谓复归京师,只是事毕复归,故亦曰『复』。前说『班瑞于群后』,即是还之也。」此二句本横渠说。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乃倒文。当云:「肆觐东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如五器,卒乃复。」五器,谓五礼之器也。如周礼大行人十一年「同数器」之谓,如即同也。「卒乃复」,言事毕则回之南岳去也。又曰:「既见东后,必先有贽见了,然后与他整齐这许多事一遍。」
问:「贽用生物,恐有飞走。」曰:「以物束缚之,故不至飞走。」
「卒乃复」,是事毕而归,非是以贽为复也。
汪季良问:「『五载一巡狩』,还是一年遍历四方,还是止于一方?」曰:「恐亦不能遍。」问:「卒乃复」。曰:「说者多以为『如五器』,『辑五瑞』,而卒复以还之,某恐不然。只是事卒则还复尔。」鲁可几问:「古之巡狩,不至如后世之千骑万乘否?」曰:「今以左氏观之,如所谓『国君以乘,卿以旅』,国君则以千五百人卫,正卿则以五百人从,则天子亦可见矣。」可几曰:「春秋之世,与茆茨土阶之时莫不同否?」曰:「也不然。如黄帝以师为卫,则天子卫从亦不应大段寡弱也。」
或问:「舜之巡狩,是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观其末后载『归格于艺祖,用特』一句,则是一年遍巡四岳矣。」问:「四岳惟衡山最远。先儒以为非今之衡山,别自有衡山,不知在甚处?」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则四岳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岁不能遍及四岳,则到一方境上会诸侯亦可。周礼有此礼。」铢录云:「唐虞时以潜山为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只往一处。」
「五载一巡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岁间行一遍,则去一方近处会一方之诸侯。如周礼所谓「十有二岁,巡狩殷国」,殷国,即是会一方之诸侯,使来朝也。又云:「巡狩,亦非是舜时创立此制,盖亦循袭将来,故黄帝纪亦云:『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舜巡狩,恐不解一年周遍得,四岳皆至远也。
巡守,只是去回礼一番。
「肇十有二州」。冀州,尧所都,北去地已狭。若又分而为幽并二州,则三州疆界极不多了。青州分为营州,亦然。叶氏曰:「分冀州西为并州,北为幽州。青州又在帝都之东,分其东北为营州。」
仲默集注尚书,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后,又并作九州岛。」曰:「也见不得。但后面皆只说『帝命式于九围』,『以有九有之师』。不知是甚时,又复并作九州岛。」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象者,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剕、宫、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纲领,诸刑之总括,犹今之刑皆结于笞、杖、徒、流、绞、斩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为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则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则加以劓刑;剕、宫、大辟,皆然。犹夷虏之法,伤人者偿创,折人手者亦折其手,伤人目者亦伤其目之类。『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轻可恕,或因过误,则全其肌体,不加刀锯,但流以宥之,屏之远方不与民齿,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类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犹今之鞭挞吏人,盖自有一项刑专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礼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类。『扑作教刑』,此一项学官之刑,犹今之学舍夏楚,如习射、习艺,『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则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挞记之类是也。『金作赎刑』,谓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则许用金以赎其罪。如此解释,则五句之义,岂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轻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轻者,有金以赎之。流宥所以宽五刑,赎刑所以宽鞭扑。圣人斟酌损益,低昂轻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无毫厘秒忽之差,所谓『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说圣人专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圣人固以教化为急。若有犯者,须以此刑治之,岂得置而不用!」问:「赎刑非古法?」曰:「然。赎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谓『赎刑』者,赎鞭扑耳。夫既已杀人伤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赎,则有财者皆可以杀人伤人,而无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杀之者安然居乎乡里,彼孝子顺孙之欲报其亲者,岂肯安于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远方,彼此两全之也。」
问:「『象以典刑』,如何为象?」曰:「此言正法。象,如『悬象魏』之『象』。或谓画为五刑之状,亦可。此段舜典载得极好,有条理,又轻重平实。『象以典刑』,谓正法,盖画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宫、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流宥五刑』,为流法,以宥犯此肉刑之正法者。盖其为恶害及平人,故虽不用正法,亦必须迁移于外。『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此二者若可悯,则又为赎刑以赎之。盖鞭、扑是罪之小者,故特为赎法,俾听赎,而不及于犯正法者。盖流以宥五刑,赎以宥鞭、扑,如此乃平正精详,真舜之法也。至穆王一例令出金以赎,便不是。不成杀人者亦止令出金而免!故萧望之赎刑议有云:『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恐开利路以伤治化。』其说极当。大率圣人作事,一看义理当然,不为苟且姑息也。」
问:「五刑,吴才老亦说是五典之刑,如所谓不孝之刑,不悌之刑。」曰:「此是乱说。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荀子有一篇专论此意,说得甚好。荀子固有不好处,然此篇却说得尽好。」
五流所以宽五刑,赎刑又所以宽鞭扑之刑。石林说亦曾入思量。郑氏说则据他意胡说将去尔。
古人赎金,只是用于鞭、扑之小刑而已,重刑无赎。到穆王好巡幸,无钱,便遂造赎法,五刑皆有赎,墨百锾,劓惟倍,剕倍差,宫六百锾,大辟千锾。圣人存此篇,所以记法之变。然其间亦多好语,有不轻于用刑底意。
或问「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书做宽恤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宽恤,如被杀者不令偿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说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谨,如断者不可续,乃矜恤之『恤』耳。」
「放驩兜于崇山」,或云在今沣州慈利县。
「殛鲧于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谓「时适在彼」是也。若曰罪之彰着,或害功败事于彼,则未可知也。大抵此等隔涉遥远,又无证据,只说得个大纲如此便了,不必说杀了。才说杀了,便受折难。
「四凶」只缘尧举舜而逊之位,故不服而抵于罪。在尧时则其罪未彰,又他毕竟是个世家大族,又未有过恶,故动他未得。
流、放、窜不是死刑。殛,伊川言,亦不是死。未见其说。
问:「舜不惟德盛,又且才嗣位未几,如『齐七政,觐四岳,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齐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圣人作处自别,故书称『三载底可绩』。」
林少颖解「徂落」云,「魂殂而魄落」,说得好。便是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底意思。如「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礼乐是可见底,鬼神是不可见底。礼是节约收缩底,便是鬼;乐是发扬舒畅底,便是神。
「尧崩,『百姓如丧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礼论之,则为为天子服三年之丧,只是畿内,诸侯之国则不然。为君为父,皆服斩衰。君,谓天子、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为君,大夫以诸侯为君,诸侯以天子为君,各为其君服斩衰。诸侯之大夫却为天子服齐衰三月,礼无二斩故也。『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达官,谓通于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长,杖,其下者不杖可知。」文蔚问:「后世不封建诸侯,天下一统,百姓当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虽有远近,闻丧虽有先后,然亦不过三月。」
问:「『明四目,达四聪』,是达天下之聪明否?」曰:「固是。」曰:「孔安国言『广视听于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为目,以天下之耳为耳之意。」
「柔远能迩。」柔远,却说得轻;能迩,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三就」,只当从古注。「五宅三居」,宅,只训居。
「惇德允元」,只是说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难」字只作平声。「任」,如字。「难任人」,言不可轻易任用人也。
问「亮采惠畴」。曰:「畴,类也,与俦同。惠畴,顺众也。『畴咨若予采』,举其类而咨询也。」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则是司空之职。「惟时懋哉!」则又勉以行百揆之事。
禹以司空宅百揆,犹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户部侍郎兼平章事模样。
问:「尧德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犹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曰:「也只是怕恁地。」又问:「『蛮夷猾夏』,是有苗否?」曰:「也不专指此。但此官为此而设。」
「敬敷五教在宽。」圣贤于事无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宽」,是欲其优游浸渍以渐而入也。
「五服三就。」若大辟则就市;宫刑,则如汉时就蚕室。在墨、劓、剕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则伤人之肌体,不可不择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蚕室尔。
「五刑三就」,用五刑就三处。故大辟弃于市,宫刑下蚕室,其它底刑,也是就个隐风处。不然,牵去当风处割了耳鼻,岂不割杀了他!
问「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项,如居四海之外,九州岛之内,或近甸,皆以轻重为差。『五服三就』,是作三处就刑。如斩人于市,腐刑下蚕室,劓、刖就僻处。盖劓、刖若在当风处,必致杀人。圣人既全其生,不忍如此。」
孟子说「益烈山泽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驱逐禽兽耳,未必使之为虞官也。至舜命作虞,然后使之养育其草木禽兽耳。
问:「命伯夷典礼,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礼是见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礼也。今太常有直清堂。」
问「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则内自直;内直,则看得那礼文分明,不胡涂也。」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
古者教人多以乐,如舜命夔之类。盖终日以声音养其情性,亦须理会得乐,方能听。
古人以乐教冑子,缘平和中正。「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古人诗只一两句,歌便衍得来长。声是宫商角征羽,是声依所歌而发,却用律以和之。如黄钟为宫,则太簇为羽之类,不可乱其伦序也。
「直而温」,只是说所教冑子要得如此。若说做教者事,则于教冑子上都无益了。
或问「诗言志,声依永,律和声」。曰:「古人作诗,只是说他心下所存事。说出来,人便将他诗来歌。其声之清浊长短,各依他诗之语言,却将律来调和其声。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调了,然后做语言去合腔子,岂不是倒了!却是永依声也。古人是以乐去就他诗,后世是以诗去就他乐,如何解兴起得人。」
「声依永,律和声。」以五声依永,以律和声之高下。
「声依永,律和声」,此皆有自然之调。沈存中以为「臣与民不要大,事与物大不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
声只有五,并二变声。律只有十二,已上推不去。「声依永,律和声。」
「堲」,只训疾,较好。
「殄行」,是伤人之行。书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歼乃雠」,皆伤残之义。
「纳言」,似今中书门下省。
问「夙夜出纳朕命惟允」。曰:「纳言之官,如今之门下审覆。自外而进入者既审之,自内而宣出者亦审之,恐『谗说殄行』之『震惊朕师』也。」
「稷契皋陶夔龙,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他掌教,掌刑,掌礼乐,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那垂与益之类,便皆是个麤啬底。圣贤所以只教他治虞、治工之属,便是他只会做这般事。
「舜生三十征庸」数语,只依古注点似好。
问:「张子以别生分类为『明庶物,察人伦』,恐未安。」曰:「书序本是无证据,今引来解说,更无理会了。」又问:「如以『明庶物,察人伦』为穷理,不知于圣人分上着得『穷理』字否?」曰:「这也是穷理之事,但圣人于理自然穷尔。」
「方设居方」,逐方各设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刘侍读以「共」为「丘」,言九丘也。
大禹谟
大禹谟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见书中,皋陶陈谟了,「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故先说「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陈昌言耳。今书序固不能得书意,后来说书者又不晓序者之意,只管穿凿求巧妙尔。
自「后克艰厥后」至「四夷来王」,只是一时说话,后面则不可知。
书中「迪」字或解为蹈,或解为行,疑只是训「顺」字。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逆,对顺,恐只当训顺也。兼书中「迪」字,用得本皆轻。「棐」字只与「匪」同,被人错解作「辅」字,至今误用。只颜师古注汉书曰:「『棐』与『匪』同。」某疑得之。尚书传是后来人做,非汉人文章,解得不成文字。但后汉张衡已将「棐」字作「辅」字使,不知如何。「王若曰」,「周公若曰」,只是一似如此说底意思。若汉书「皇帝若曰」之类,盖是倡导德意者敷演其语,或录者失其语而退记其意如此也。「忱」、「谌」并训信,如云天不可信。
当无虞时,须是儆戒。所儆戒者何?「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人当无虞时,易至于失法度,游逸淫乐,故当戒其如此。既知戒此,则当「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如此,方能「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
「儆戒无虞」至「从己之欲」,圣贤言语,自有个血脉贯在里。如此一段,他先说「儆戒无虞」,盖「制治未乱,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时,必儆必戒。能如此,则不至失法度、淫于逸、游于乐矣。若无个儆戒底心,欲不至于失法度、不淫逸、不游乐,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后可以知得贤者、邪者、正者、谋可疑者、无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颠倒,便会以不贤为贤,以邪为正,所当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盖此三句,便是从上面有三句了,方会恁地。又如此,然后能「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盖于贤否、邪正、疑审,有所未明,则何者为道,何者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欲哉?
问:「『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水,如堤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内火、禁焚莱之类;木,如斧斤以时之类。」良久,云:「古人设官掌此六府,盖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出之民,用财无节也。『戒之用休』,言戒谕以休美之事。『劝之以九歌』,感动之意。但不知所谓『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说纲目,其详不可考矣。」
「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
刘潜夫问:「『六府三事』,林少颖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吴才老说『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说是。」又问「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并九歌。曰:「正是『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叙可歌,想那时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见。」
「念兹在兹,释兹在兹」,用舍皆在于此人。「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语默皆在此人。名言,则名言之;允出,则诚实之所发见者也。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过于惨刻。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以宽大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虽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愈众;虽曰仁之,适以害之。
圣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礼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书说「刑期于无刑」,只是存心期于无,而刑初非可废。又曰:「钦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说「恤刑」。
「罪疑惟轻」,岂有不疑而强欲轻之之理乎?王季海当国,好出人死罪以积阴德,至于奴与佃客杀主,亦不至死。广录云:「岂有此理!某尝谓,虽尧舜之仁,亦只是『罪疑惟轻』而已。」
或问「人心、道心」之别。曰:「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则危而易陷,道心则微而难着。微,亦微妙之义。」学蒙。
舜功问「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危。盖从形体上去,泛泛无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故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盖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之所在,无所向,若执定柁,则去住在我。」
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饥欲食、寒欲衣之心尔,如何谓之危?既无义理,如何不危?士毅。
问:「『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方子录云:「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辞。子静说得是。」又问:「圣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圣人全是道心主宰,时举录云:「圣人纯是道心。」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圣罔念作狂。』又问:「此『圣』字,寻常只作通明字看,说得轻。」曰:「毕竟是圣而罔念,便狂。」时举录同。
道心是知觉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觉得声色臭味底,人心不全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应只下个「危」字。盖为人心易得走从恶处去,所以下个「危」字。若全不好,则是都倒了,何止于危?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非有两个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不同。「惟精、惟一」,是两截工夫;精,是辨别得这个物事;一,是辨别了,又须固守他。若不辨别得时,更固守个甚么?若辨别得了又不固守,则不长远。惟能如此,所以能合于中道。又曰:「『惟精惟一』,犹『择善而固执之』。」
人心亦只是一个。知觉从饥食渴饮,便是人心;知觉从君臣父子处,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起底见识,或作「从形体上生出来底见识」。便是人心;义理上起底见识,或作「就道理上生出来底见识」。便是道心。心则一也,微则难明。有时发见些子,使自家见得,有时又不见了。惟圣人便辨之精,守得彻头彻尾,学者则须是『择善而固执之』。」
「道心是义理上发出来底,人心是人身上发出来底。虽圣人不能无人心,如饥食渴饮之类;虽小人不能无道心,如恻隐之心是。但圣人于此,择之也精,守得彻头彻尾。」问:「如何是『惟微』?」曰:「是道心略瞥见些子,便失了底意思。『惟危』,是人心既从形骸上发出来,易得流于恶。」
问「人心、道心」。曰:「如喜怒,人心也。然无故而喜,喜至于过而不能禁;无故而怒,怒至于甚而不能遏,是皆为人心所使也。须是喜其所当喜,怒其所当怒,乃是道心。」问:「饥食渴饮,此人心否?」曰:「然。须是食其所当食,饮其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而道心亡矣!」问:「人心可以无否?」曰:「如何无得!但以道心为主,而人心每听命焉耳。」
饥食渴饮,人心也;如是而饮食,如是而不饮食,道心也。唤做人,便有形气,人心较切近于人。道心虽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难见。道心如清水之在浊水,惟见其浊,不见其清,故微而难见。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则思」,故贵「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见那边利害情欲之私,道心只见这边道理之公。有道心,则人心为所节制,人心皆道心也。
吕德明问「人心、道心」。曰:「且如人知饥渴寒暖,此人心也;恻隐羞恶,道心也。只是一个心,却有两样。须将道心去用那人心,方得。且如人知饥之可食,而不知当食与不当食;知寒之欲衣,而不知当衣与不当衣,此其所以危也。」
饥欲食,渴欲饮者,人心也;得饮食之正者,道心也。须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间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见了。人心与道心为一,恰似无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纯一,道心都发见在那人心上。
问「人心、道心」。曰:「饮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义,万锺不取,道心也。若是道心为主,则人心听命于道心耳。」
问:「人心、道心,如饮食男女之欲,出于其正,即道心矣。又如何分别?」曰:「这个毕竟是生于血」
问:「『人心惟危』,则当去了人心否?」曰:「从道心而不从人心。」
道心,人心之理。
心,只是一个心,卓录云:「人心、道心,元来只是一个。」只是分别两边说,人心便成一边,道心便成一边。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卓作「专」。既能辨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这中是无过不及之中。
自人心而收之,则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近之。骧。
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将。
问:「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已发见,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
问「道心惟微」。曰:「义理精微难见。且如利害最易见,是粗底,然鸟兽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争些子。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义刚录见下。
林武子问:「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气所有,但地步较阔。道心却在形气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细底便难见,麤底便易见。饥渴寒暖是至麤底,虽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较细者言之,如利害,则禽兽已有不能知者。若是义理,则愈是难知。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言所争也不多。」
人心者,气质之心也,可为善,可为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惟精」是无杂,「惟一」是终始不变,乃能「允执厥中」。
人心是知觉,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若便说做人欲,则属恶了,何用说危?道心是知觉义理底;「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隐。「惟精」是要别得不杂,「惟一」是要守得不离。「惟精惟一」,所以能「允执厥中」。
问:「微,是微妙难体;危,是危动难安否?」曰:「不止是危动难安。大凡[犬旬]人欲,自是危险。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万里之外。庄子所谓『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动不动便是堕坑落堑,危孰甚焉!」文蔚曰:「徐子融尝有一诗,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须别人心与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紧。当云:『须知妙旨存精一,正为人心与道心。』」又问「精一」。曰:「精是精别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颜子择中庸处,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处,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此语甚好。」
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此言尽之矣。惟精者,精审之而勿杂也;惟一者,有首有尾,专一也。此自尧舜以来所传,未有他议论,先有此言。圣人心法,无以易此。经中此意极多,所谓「择善而固执之」,择善,即惟精也;固执,即惟一也。又如「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笃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诚之」,便是惟一也。大学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诚意,则惟一矣。学则是学此道理。孟子以后失其传,亦只是失此。
问:「惟精惟一」。曰:「人心直是危,道心直是微。且说道心微妙,有甚准则?直是要择之精!直是要守之一!」
因论「惟精惟一」曰:「虚明安静,乃能精粹而不杂;诚笃确固,乃能纯一而无间。」
「惟精惟一」,舜告禹,所以且说行;不似学者而今当理会精也。
精,是识别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允执,只是个真知。
问「精一执中」之说。曰:「惟精,是精察分明;惟一,是行处不杂;执中,是执守不失。」
汉卿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段。曰:「凡事有一半是,一半不是,须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却要守得彻头彻尾。惟其如此,故于应事接物之际,头头捉着中。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废。」杞。
问:「尧舜禹,大圣人也。『允执厥中』,『执』字似亦大段吃力,如何?」曰:「圣人固不思不勉。然使圣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则罔念而作狂矣!经言此类非一,更细思之。」
符舜功问:「学者当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计。不如只于天理上做功夫,人欲自消。」曰:「尧舜说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于两者交界处理会。尧舜时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诀只如此。」方伯谟云:「人心道心,伊川说,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两物,如两个石头样,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当于其分界处理会。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说得最好。及至理会了精底、一底,只是一个人。」又曰:「『执中』是无执之『执』。如云:『以尧舜之道要汤』,何曾『要』来?」可学录别出。
舜功问:「人多要去人欲,不若于天理上理会。理会得天理,人欲自退。」曰:「尧舜说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界处,不是两个。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须是在天理则存天理,在人欲则去人欲。尝爱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此语甚好。」舜功云:「陆子静说人心混混未别。」曰:「此说亦不妨。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观下文『惟精惟一』可见。」德粹问:「既曰『精一』,何必云『执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一,则信乎其能执中也。」因举子静说话多反伊川。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解云:「『惟其深喻,是以笃好。』渠却云『好而后喻』,此语亦无害,终不如伊川。」通老云:「伊川云:『敬则无己可克。』」曰:「孔门只有个颜子,孔子且使之克己,如何便会不克?此语意味长!」
舜禹相传,只是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只就这心上理会,也只在日用动静之间求之,不是去虚中讨一个物事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便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便在日用间。存养,是要养这许多道理在中间,这里正好着力。
林恭甫说「允执厥中」,未明。先生曰:「中,只是个恰好底道理。允,信也,是真个执得。尧当时告舜时,只说这一句。后来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是舜说得又较子细。这三句是『允执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处。说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须是『惟精惟一』,方能『允执厥中』。尧当时告舜,只说一句。是时舜已晓得那个了,所以不复更说。舜告禹时,便是怕禹尚未晓得,故恁地说。论语后面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之类,皆是恰好当做底事,这便是执中处。尧舜禹汤文武治天下,只是这个道理。圣门所说,也只是这个。虽是随他所问说得不同,然却只是一个道理。如屋相似,进来处虽不同,入到里面,只是共这屋。大概此篇所载,便是尧舜禹汤文武相传治天下之大法。虽其纤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却于此可见。」次日,恭甫又问:「道心,只是仁义礼智否?」曰:「人心便是饥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饥而思食后,思量当食与不当食;寒而思衣后,思量当着与不当着,这便是道心。圣人时那人心也不能无,但圣人是常合着那道心,不教人心胜了道心。道心便只是要安顿教是,莫随那人心去。这两者也须子细辨别,所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个便须是常常戒慎恐惧,精去拣择。若拣得不精,又便只是人心。大概这两句,只是个公与私;只是一个天理,一个人欲。那『惟精』,便是要拣教精;『惟一』,便是要常守得恁地。今人固有其初拣得精,后来被物欲引从人心去,所以贵于『惟一』。这『惟精惟一』,便是舜教禹做工夫处。它当时传一个大物事与他,更无他说,只有这四句。且如『仁者先难而后获』,那『先难』便是道心,『后获』便是人心。又如『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说仁义时,那不遗亲而后君自在里面了。若是先去计较那不遗亲,不后君,便是人心,便不是天理之公。」义刚问:「『惟精惟一』,也是就心上说否?」曰:「也便是就事说。不成是心里如此,临事又别是个道理。有这个心,便有这个事;因有这个事后,方生这个心。那有一事不是心里做出来底?如口说话,便是心里要说。如『紾兄之臂』,你心里若思量道不是时,定是不肯为。」
问:「曾看无垢文字否?」某说:「亦曾看。」问:「如何?」某说:「如他说:『「动心忍性」,学者当惊惕其心,抑遏其性。』如说『「惟精惟一」,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专致而不二』。」曰:「『深入』之说却未是。深入从何处去?公且说人心、道心如何?」某说:「道心者,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所谓『寂然不动』者也;人心者,喜怒哀乐已发之时,所谓『感而遂通』者也。人当精审专一,无过不及,则中矣。」曰:「恁地,则人心、道心不明白。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物物上有个天理人欲。」因指书几云:「如墨上亦有个天理人欲,砚上也有个天理人欲。分明与他劈做两片,自然分晓。尧舜禹所传心法,只此四句。」」德明录别出。
窦初见先生,先生问前此所见如何,对以「欲察见私心」云云。因举张无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专志而无二。』亦自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别得界限分明。彼所谓『深入』者,若不察见,将入从何处去?」窦曰:「人心者,喜怒哀乐之已发,未发者,道心也。」曰:「然则已发者不谓之道心乎?」窦曰:「了翁言:『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曰:「然则人心何以谓之『危』?道心何以谓之『微』?」窦曰:「未发隐于内,故微;发不中节,故危。是以圣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此处举语录前段。所谓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圣人以此二者对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专一守着一个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两片,便知得一个好,一个恶。尧舜所以授受之妙,不过如此。」
问「允执厥中」。曰:「书传所载多是说无过、不及之中。只如中庸之『中』,亦只说无过、不及。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一处,却说得重也。」
既「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又曰「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因言舜禹揖逊事,云:「本是个不好底事。被他一转,转作一大好事!」
舞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于度外,而示以闲暇之意。
皋陶谟
问:「『允迪厥德,谟明弼谐』,说者云,是形容皋陶之德,或以为是皋陶之言。」曰:「下文说『慎厥身修,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庶明励翼』,是『谟明弼谐』意。恐不是形容皋陶底语。」问:「然则此三句是就人君身上说否?」曰:「是就人主身上说。谟,是人主谋谟;弼,是人臣辅翼,与之和合,如『同寅协恭』之意。」
「庶明励翼」,庶明,是众贤样,言赖众明者勉励辅翼。
问「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难晓。若且据文势解之,当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言其人之有德,当以事实言之。古注谓『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为验』,是也。」
九德分得细密。
皋陶九德,只是好底然须两件凑合将来,方成一德,凡十八种。
或问:「圣贤教人,如『克己复礼』等语,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不见有教人变化气质处,如何?」曰:「『宽而栗,柔而立,刚而无虐』,这便是教人变化气质处。」又曰:「有人生下来便自少物欲者,看来私欲是气质中一事。」
「简而廉」,廉者,隅也;简者,混而不分明也。论语集注:「廉,谓棱角峭厉」,与此『简者,混而不分明』相发。」寿昌。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当处者,谓之叙;因其叙而与之以其所当得者,谓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里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这个叙,便是他这个自然之秩。
「天工人其代之。」「天秩、天叙、天命、天讨」,既曰「天」,便自有许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个分不同。
「同寅协恭」,是上下一于敬。
「同寅协恭」,是言君臣。「政事懋哉!懋哉!」即指上文「五礼、五刑」之类。
要「五礼有庸」,「五典五惇」,须是「同寅协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须是「政事懋哉!懋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德之大者,则赏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则赏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则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则罪以小底刑,尽是「天命、天讨」,圣人未尝加一毫私意于其间,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许多典礼,都是天叙天秩下了,圣人只是因而敕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谓冠昏丧祭之礼,与夫典章制度,文物礼乐,车舆衣服,无一件是圣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圣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将去。如推个车子,本自转将去,我这里只是略扶助之而已。
益稷
问:「益稷篇,禹与皋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夔前面且做是脱简,后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时,只是说他无可言,但『予思日孜孜』。皋陶问他如何,他便说也要恁地孜孜,却不知后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说那丹朱后,故恁地说。丹朱缘如此,故不得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教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顾后。」
「止」,守也。「惟几」,当审万事之几;「惟康」,求个安稳处。「弼直」,以直道辅之应之。非惟人应之,天亦应之。
张元德问:「『惟几惟康,其弼直』,东莱解『几』作『动』,『康』作『静』,如何?」曰:「理会不得。伯恭说经多巧。」良久,云:「恐难如此说。」问元德:「寻常看『予克厥宅心』,作存其心否?」曰:「然。」曰:「若说『三有俊心,三有宅心』,曰『三有宅,三有俊』,则又当如何?此等处皆理会不得。解得这一处,碍了那一处。若逐处自立说解之,何书不可通!」良久,云:「宅者,恐是所居之位,是已用之贤;俊者,是未用之贤也。」元德问「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曰:「亦不可晓。汉书『在治忽』作『七始咏』,七始,如七均之类。又如『工以纳言,时而扬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一段,上文说:『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皆不可晓。如命龙之辞亦曰:『朕圣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皆言谗说。此须是当时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当杜撰胡说,只得置之。」元德谓「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乃是赏罚。曰:「既是赏罚,当别有施设,如何只靠射?岂有无状之人,纔射得中,便为好人乎?」元德问:「『五言』,东莱释作君臣民事物之言。」曰:「君臣民事物是五声所属,如『宫乱则荒,其君骄』。宫属君,最大,羽属物,最小,此是论声。若商,放缓便似宫声。寻常琴家最取广陵操,以某观之,其声最不和平,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纳五言』,却恐是审乐知政之类。如此作五言说,亦颇通。」又云:「纳言之官,如汉侍中,今给事中,朝廷诰令,先过后省,可以封驳。」元德问:「孔壁所传本科斗书,孔安国以伏生所传为隶古定,如何?」曰:「孔壁所传平易,伏生书多难晓。如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是伏生所传,有『方鸠僝功』,『载采采』等语,不可晓。大禹谟一篇却平易。又书中点句,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宁王遗我大宝龟』,『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与古注点句不同。又旧读『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作一句。今观古记款识中多云『俊在位』,则当于『寿』字绝句矣。」又问:「盘庚如何?」曰:「不可晓。如『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全无意义。又当时迁都,更不说明迁之为利,不迁之为害。如中篇又说神说鬼。若使如今诰令如此,好一场大鹘突!寻常读尚书,读了太甲伊训咸有一德,便着鞔过盘庚,却看说命。然高宗肜日亦自难看。要之,读尚书,可通则通;不可通,姑置之。」
义刚点尚书「作会」作一句。先生曰:「公点得是。」
「明庶以功」,恐「庶」字误,只是「试」字。
「苗顽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时,调役他国人夫不动也。后方征之。既格而服,则治其前日之罪而窜之,窜之而后分北之。今说者谓苗既格而又叛,恐无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数种,一种谓之『媌』,未必非三苗之后也。史中说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