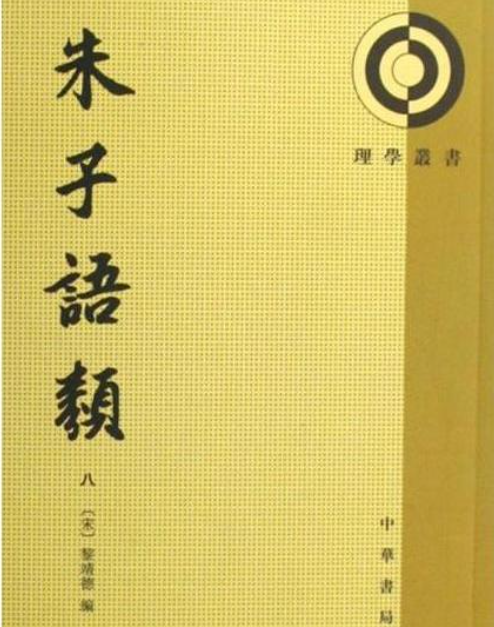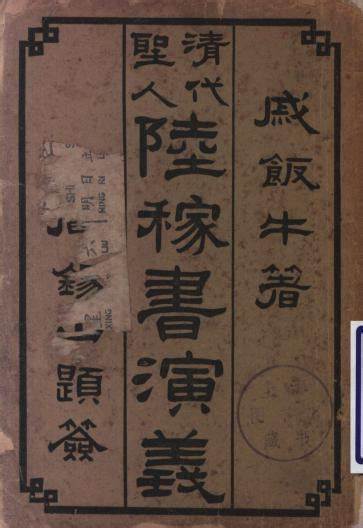论语二十一
先进篇上
先进于礼乐章
立之问:「先进、后进,于礼乐文质何以不同?」曰:「礼,只是一个礼,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逊,古人只是诚实依许多威仪行将去,后人便自做得一般样忒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谨节,后人便近于巧言、令色。乐,亦只是一个乐,亦是用处自不同。古乐不可得而见矣。只如今人弹琴,亦自可见。如诚实底人弹,便雍容平淡,自是好听。若弄手弄脚,撰出无限不好底声音,只见繁碎耳。」因论乐:「黄锺之律最长,应锺之律最短,长者声浊,短者声清。十二律旋相为宫,宫为君,商为臣。乐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声。如今响板子有十六个,十二个是正律,四个是四清声。清声是减一律之半。如应锺为宫,其声最短而清。或蕤宾为商,则是商声高似宫声,是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宾律减半为清声以应之。虽然减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应也。此是通典载此一项。徽宗朝作大晟乐,其声是一声低似一声,故其音缓散。太祖英明不可及。当王朴造乐时,闻其声太急,便令减下一律,其声遂平。」
问:「『先进于礼乐』,此礼乐还说宗庙、朝廷以至州、闾、乡、党之礼乐?」曰:「也不止是这般礼乐。凡日用之间,一礼一乐,皆是礼乐。只管文胜去,如何合杀!须有个变转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时,通上位书启,只把纸封。后来做书盝,如今尽用紫罗背盝,内用真红。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杀!」问:「孔子又云:『吾」』只是指周之前辈而言?」曰:「然。圣人穷而在下,所用礼乐,固是从周之前辈。若圣人达而在上,所用礼乐,须更有损益,不止从周之前辈。若答颜子为邦之问,则告以四代之礼乐。」问:「如孔子所言:『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又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此皆欲损过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语最多。」又云:「观圣人意思,因见得事事都如此,非独礼乐。如孟子后面说许多乡原、狂狷,亦是此意。乡原直是不好,宁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细密,倒未必好,宁可是白直粗疏底人。」
夫子于礼乐欲从先进。今观礼书所载燕飨之礼,品节太繁,恐亦难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删修,使之合义。如乡饮酒礼,向来所行,真成强人,行之何益!所以难久。不若只就今时宴饮之礼中删改行之,情意却须浃洽。
从我于陈蔡章
问「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曰:「此说当从明道。谓此时适皆不在孔子之门,思其相从于患难,而言其不在此耳。门人记之,因历数颜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长云耳。」
问:「德行,不知可兼言语、文学、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项上看。如颜子之德行,固可以备;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于才者。」因云:「冉伯牛闵子之德行,亦不多见。子夏子游两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峰说,不知集注中载否。他说子夏是循规守矩,细密底人;子游却高朗,又欠细密工夫。荀子曰:『第作其冠,神谭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懦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如学子游之弊,只学得许多放荡疏阔意思。」贺孙因举如「丧至乎哀而止」,「事君数,斯辱;朋友数,斯疏」,皆是子游之言。如「小子当洒埽应对进退」等语,皆是子夏之言。又如子游能养而不能敬,子夏能敬而少温润之色,皆见二子气象不同处。曰:「然。」
问「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别。曰:「德行是个兼内外、贯本末、全体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见于用者也。」
德行,得之于心而见于行事者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旧曾问李先生,颜子非助我者处。李先生云:「颜子于圣人根本有默契处,不假枝叶之助也。如子夏,乃枝叶之功。」
南容三复白圭章
先生令接读问目「南容三复白圭」。云:「不是一旦读此,乃是日日读之,玩味此诗而欲谨于言行也。此事见家语,自分明。」
颜路请子之车章
郑问:「颜渊死,孔子既不与之车,若有钱,还亦与之否?」曰:「有钱亦须与之,无害。」
问:「注以为命车,何以验之?」曰:「礼记言,大夫赐命车。」
门人厚葬章
「门人厚葬」,是颜子之门人。「不得视犹子」,以有二三子故也,叹不得如葬鲤之得宜。此古注说得甚好,又简径。
季路问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
或问「季路问鬼神」章。曰:「事君亲尽诚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则『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具无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
或问:「二气五行,聚则生,散则死;聚则不能不散,如昼之不能不夜。故知所以生,则知所以死。苟于事人之道未能尽,焉能事鬼哉?」曰:「不须论鬼为已死之物。但事人须是诚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事其所当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则谄矣。」
问:「人鬼一理。人能诚敬,则与理为一,自然能尽事人、事鬼之道。有是理,则有是人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是如此否?」曰:「人且从分明处理会去。如诚敬不至,以之事人,则必不能尽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晓其所以生,则又焉能晓其所以死乎!」
亚夫问「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才说破,则人便都理会得。然须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禀五常之性以来,所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者,须要一一尽得这生底道理,则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张子所谓『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是也。」
问:「天地之化,虽生生不穷,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则必知其后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气化之日,初无精神寄寓于太虚之中;则知其死也,无气而俱散,无复更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内。」曰:「死便是都散无了。」
或问「季路问鬼神」章。曰:「世间无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时是这模样,则散时也是这模样。若道孔子说与子路,又不全与他说;若道不说,又也只是恁地。」
先生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曾以一时趋平原者言之:「我于人之不当事者,不妄事,则于鬼神亦然。所以程子云:『能尽事人之道,则能尽事鬼之道,一而二,二而一。』」
问:「伊川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气与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则有是气;有是气,则有是理。气则二,理则一。」
徐问:「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在人事中,何以见?」曰:「鬼神只是二气屈伸往来。在人事,如福善祸淫,亦可见鬼神道理。论语少说此般话。」曰:「动静语默,亦是此理否?」曰:「亦是。然圣人全不曾说这般话与人,以其无形无影,固亦难说。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只如此说而已。」今集注无。
闵子侍侧章
问闵子誾誾,冉有子贡侃侃,二者气象。曰:「闵子纯粹,冉有子贡便较粗了。侃侃,便有尽发见在外底气象。闵子则较近里些子。」雄。
问:「『冉有子贡侃侃如也。』这『侃侃』字,只作刚直说,如何?」曰:「也只是刚直。闵子骞气象便自深厚。冉有子贡便都发见在外。」
「冉有子贡,侃侃如也。」侃侃,刚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气象观之。赐之达,求之艺,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这般气象。闵子纯于孝,自然有誾誾气象。
誾誾,是深沉底;侃侃,是发露圭角底;行行,是发露得粗底。
问:「『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刚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个退逊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异:求赐则微见其意,子路则全体发在外,闵子则又全不外见,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问,有怀必吐,无有遮覆含糊之意。」曰:「岂非以卑承尊,易得入于柔佞卑谄;三子各露其情实如此,故夫子乐之?」曰:「都无那委曲回互底意思。」
问「誾誾、行行、侃侃」。曰:「闵子于和悦中,却有刚正意思。仲由一于刚正。闵子深厚,仲由较表露。」问「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辞。圣人虽谓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变其气习,亦必有以处死。」
吴伯英讲「由也不得其死」处,问曰:「由之死,疑其甚不明于大义。岂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没紧要。然误处不在致死之时,乃在于委质之始。但不知夫子既教之以正名,而不深切言其不可仕于卫,何欤?若冉有子贡则能问夫子为卫君与否,盖不若子路之粗率。」
或问:「子路死于孔悝之难,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呆。出公岂可仕也!」又问:「若仕于孔悝,则其死为是否?」曰:「未问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于卫,自不是了。况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见得可仕于大夫,而不知辄之国非可仕之国也。」问:「孔门弟子多仕于列国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别无科阙,仕进者只有此一门,舍此则无从可仕,所以颜闵宁不仕耳。」
子路死孔悝之难,未为不是;只是他当初事孔悝时错了,到此不得其死。饶本作:「到此只得死。」卫君不正,冉有子贡便能疑而问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圣人说话。「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卫。他更说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圣人已见得他错了,但不如鸣鼓攻之,责得求之深。虽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说,然终不分晓痛说与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晓,不知圣人何故不痛责之?
子路为人粗,于精微处多未达。其事孔悝,盖其心不以出公为非故也。悝即出公之党。何以见得他如此?如「卫君待子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为迂,可见他不以出公为非。故其事悝,盖自以为善而为之,而不知其非义也。
子贡问师与商也章
问:「『师也过,商也不及。』看过与不及处,莫只是二子知见上欠工夫?」曰:「也不独知见上欠,只二子合下资质是这模样。子张便常要将大话盖将去,子夏便规规谨守。看论语中所载子张说话,及夫子告子张处,如『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之类。如子张自说:『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说话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说得这般话。这是大贤以上,圣人之事,他便把来盖人,其疏旷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无为小人儒』;又云『无欲速,无见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当洒埽应对进退』之类,可见。」又问:「『参也,竟以鲁得之。』鲁,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参虽鲁,而规模志向自大,所以终能传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浅狭,而不能穷究道体之大全,所以终于不及。」曰:「鲁,自与不及不相似。鲁是质朴浑厚意思,只是钝;不及底恰似一个物事欠了些子。」
问:「伊川谓师商过、不及,其弊为杨墨。」曰:「不似杨墨。墨氏之学,萌櫱已久,晏子时已有之矣。师商之过、不及,与兼爱、为我不关事。」
季氏富于周公章
问:「以季氏之富,『而求也为之聚敛』。」曰:「不问季氏贫富。若季氏虽富,而取于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当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说。」
问:「冉求圣门高弟,亲炙圣人,不可谓无所见。一旦仕于季氏,『为之聚敛而附益之』。盖缘他工夫间断,故不知不觉做到这里,岂可不时时自点检!」曰:「固是。只缘个公私义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若是常在界分内做,自然不到如此。纔出界分去,则无所不至矣。」
问「季氏富于周公」一章。先生令举范氏之说,叹美久之。云:「人最怕资质弱。若过于刚,如子路虽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气英风,尚足以起顽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岂不知爱民,而反为季氏聚敛。如范氏云:『其心术不明。』惟是心术不明,到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为急。』他只缘以仕为急,故从季氏。见他所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从其恶。」贺孙因云:「若闵子『善为我辞』之意,便见得煞」曰:「然。」因云:「谢氏说闵子处最好。」因令贺孙举读全文。曰:「冉求路头错处,只在急于仕。人亦有多样,有一等人合下只是要求进;又有一等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见此事自匹似闲;又有一等人虽要求进,度其不可,亦有退步之意。」
柴也愚章
「柴也愚。」他是个谨厚底人,不曾见得道理,故曰愚。
吴伯英问「柴也愚」,因说:「柴尝避难于卫,不径不窦。使当时非有室可入,则柴必不免,此还合义否?」曰:「此圣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于匡,微服过宋,料须不如此。」
用之问高子羔不窦不径事。曰:「怕圣人须不如此。如不径不窦,只说平安无事时若当有寇赋患难,如何专守此以残其躯,此柴之所以为愚。圣人『微服而过宋』。微服,是着那下贱人衣服。观这意如此,只守不径不窦之说不得。如途中万一遇大盗贼,也须走避,那时如何要不由小径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学到变通处,尽好,止缘他学有未尽处。」问:「学到时,便如曾子之易箦?」曰:「易箦也只是平常时」又曰:「『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不可为政者,正缘他未能应变,他底却自正。」问:「子路之死,与子羔事如何?」曰:「子路事更难说。」又曰:「如圣节,就祝寿处拜四拜。张忠甫不出仕,尝曰:『只怕国忌、圣节,去拜佛不得。』这也如不窦不径相似。」因说:「国家循袭这般礼数,都晓不得。往往拜佛之事,始于梁武帝,以私忌设斋,始思量圣节要寓臣子之意,又未有个所在奉安。」又曰:「尊号始于唐德宗,后来只管循袭。若不是人主自理会得,如何说。当神宗时,群臣上尊号,司马温公密撰不允诏书,劝上不受,神宗便不受。这只是神宗自见得,虽温公也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丧,其废如此长远,寿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见有甚不可行处。」
「参也鲁。」鲁,是鲁钝。曾子只缘鲁钝,被他不肯放过,所以做得透。若是放过,只是鲁而已。
读「参也鲁」一段,云:「只曾子资质自得便宜了。盖他以迟钝之故,见得未透,只得且去理会,终要洞达而后已。若理会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则是终于鲁而已。」
「参也,竟以鲁得之。」曾子鲁钝难晓,只是他不肯放过,直是捱得到透彻了方住;不似别人,只略绰见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样敏底见得容易,又不能坚守;钝底捱得到略晓得处,便说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更不放舍,若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尽处,所以竟得之。
明道谓曾子「竟以鲁得之」。缘他质钝,不解便理会得,故着工夫去看,遂看得来透彻,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见得虽快,然只是从皮肤上略过,所以不如他。且莫说义理,只如人学做文章,非是只恁地读前人文字了,便会做得似他底;亦须是下工夫,始造其妙。观韩文公与李翊书,老苏与欧阳公书,说他学做文章时,工夫甚么细密!岂是只恁从册子上略过,便做得如此文字也。毅略。
「参也,竟以鲁得之。」不说须要鲁。鲁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却尚是个好底病。就他说,却是得这个鲁底力。
「参也,竟以鲁得之。」鲁钝则无造作。
曾子以鲁得之,只是鲁钝之人,却能守其心专一。明达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专一。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问:「『回也,其庶乎;屡空。』大意谓颜子不以贫窭动其心,故圣人见其于道庶几。子贡不知贫富之定命,而于贫富之间不能无留情,故圣人见其平日所讲论者多出亿度而中。」曰:「据文势也是如此。但颜子于道庶几,却不在此。圣人谓其如此,益见其好。子贡不受命,也在平日,圣人亦不因其货殖而言。」贺孙因问:「集注云,颜回,言其乐道,又能安贫。以此意看,若颜子不处贫贱困穷之地,亦不害其为乐。」曰:「颜子不处贫贱,固自乐;到他处贫贱,只恁地更难,所以圣人于此数数拈掇出来。」
颜子屡空,说作「空中」,不是。论语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说无所得,别不见说虚空处。
问:「『屡空』,前辈及南轩皆作空无说,以为『无意、必、固、我』之『无』。但颜子屡空,未至于圣人之皆无而纯然天理也。及先生所解,却作屡空乏而自乐,何也?」曰:「经意当如此。不然,则连下文子贡作二段事。空无之说,盖自何晏有此解。晏,老氏清净之学也。因其有此说,后来诸公见其说得新好,遂发明之。若颜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屡无,只是此经意不然。颜子不以贫乏改其乐而求其富。如此说,下文见得子贡有优劣。」
问:「吕曰:『货殖之学,聚所闻见以度物,可以屡中,而不能悉中。』尝记前辈一说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贡于货殖,下与马医、夏畦同科,谓其「所至,诸侯莫不分庭抗礼」,天下后世无不指子贡为竖贾之事。子贡,孔门高弟,岂有圣人之门,而以贾竖为先乎!屡空,无我者也,其学则自内而求。货殖,自外而入,非出于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于见闻者莫不解悟,比之屡空者为有间矣。』」曰:「此说乃观文叶公所作,审是集中之语,盖吕与叔之遗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盖屡空者,『空乏其身』也。货殖,则对屡空而言,不能不计较者是也。范氏曰:『颜子箪食瓢饮屡绝,而不改其乐,天下之物岂有能动其心者!』此说为得之。」
子张问善人之道章
问「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个善人底道理。所谓善人者,是天资浑然一个好人,他资质至善而无恶,即『可欲之谓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于恶。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尽善流而为恶。但他既天资之善,故不必循涂守辙,行之皆善。却缘只是如此而无学,故不能入圣人阃室。横渠之解极好。」涂辙,犹言规矩尺度。
味道问:「善人只是好资质,全未曾学。」曰:「是。」又问:「不践迹」。曰:「是古人所做底事恁地好。虽不曾学古人已做底事,做得来也恁地好。『循涂守彻』,犹言循规守矩云耳。」
「践迹」,迹是旧迹,前人所做过了底样子,是成法也。善人虽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样子,效他去做,但所为亦自与暗合,但未能到圣人深处。
施问「不践迹」。曰:「是他资质美,所为无个不是;虽不践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晓会,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学问,所以『亦不入于室』。」林问:「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奥处。」
问「不践迹」。曰:「善人质美,虽不学样子,却做得是。然以其不学,是以不入室,到圣人地位不得。」谦之。
善人乃是天资自然有善者,不待循常迹,而自然能有其善。然而不能加学,则亦不足以入圣人之室。震。
谢教问「不践迹」。曰:「资质美,只是暗合,不依本子做。横渠说得好。然亦只是终于此而已。」
问:「『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莫是笃行之而后可以入善之阃奥否?」曰:「若如此言,却是说未为以前事。今只说善人只是一个好底资质,不必践元本子,亦未入于室。须是要学,方入圣贤之域。惟横渠云:『志于仁而无恶。』此句最尽。如乐正子,自『可欲』之善人去,自可到『美、大、圣、神』地位。」
问:「善人莫是天资好人否?故虽不必循守旧人涂辙,而自不为恶。然其不知学问,故亦不能入于圣人之室。此可见美质有限,学问无穷否?」曰:「然。」
问:「寻常解『践迹』,犹踏故步。『不践迹』者,亦有所进;『亦不入于室』者,所进不远也。今集注解『践迹』,不循样辙之意,如何?」曰:「善人者以其心善,故不假成法,而其中自能运用,故曰『不践迹』。据此,止说善人未有进意。」洽。
问:「不践迹何以为善人?」曰:「不循习前人已试之法度,而亦可以为善,如汉文帝是也。」
魏才仲问「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谓『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之类。」又问:「如太史公赞文帝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为他截断,只到这里,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说道不依样子,也自不为恶,只是不能入圣人之室。」又问:「文帝好黄老,亦不免有惨酷处。莫是纔好清净,便至于法度不立,必至惨酷而后可以服人?」曰:「自清净至惨酷,中间大有曲折,却如此说不得。唯是自家好清净,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问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这里更不与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为惨酷。」伯谟曰:「黄老之教,本不为刑名,只要理会自己,亦不说要惨酷,但用之者过耳。」曰:「缘黄老之术,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让别人,宁可我杀了你,定不容你杀了我。他术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犹善用之,如南越反,则卑词厚礼以诱之;吴王不朝,赐以几杖等事。这退一着,都是术数。到他教太子,晁错为家令。他谓太子亦好学,只欠识术数,故以晁错傅之。到后来七国之变,弄成一场纷乱。看文景许多慈祥岂弟处,都只是术数。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子畏于匡章
或问:「『回何敢死』,伊川改『死』为『先』,是否?」曰:「伊川此话,门人传之恐误,其间前后有相背处。今只作『死』字说。其曰『吾以汝为死矣』者,孔子恐颜回遇害,故有此语。颜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颜子谓孔子既得脱祸,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则颜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问:「颜路在,颜子许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与不许友以死之意别。不许以死,在未处难以前乃可。如此处已遇难,却如此说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