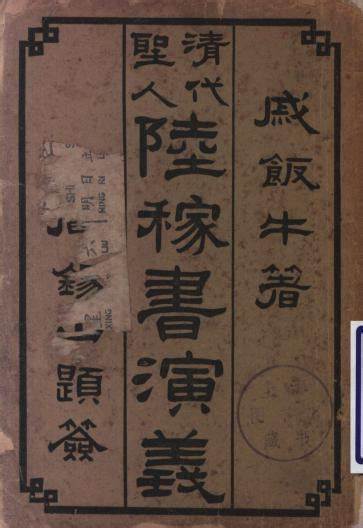罗氏门人
李愿中
李先生终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无隤堕之
延平先生气象好。
问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书,充养得极好。凡为学,也不过是恁地涵养将去,初无异义。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骧。
李延平初间也是豪迈底人,到后来也是磨琢之功。在乡,若不异于常人,乡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个善人。他也略不与人说。待问了,方与说。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问:「先生如何养?」曰:「先生只是潜养思索。」
「人性褊急,发不中节者,当于平日言语动作间以缓持之。持之久,则心中所发,自有条理。」因说:「李先生行郊外,缓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计其远。尝随至人家,才相见,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罢,即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厅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毕就坐。其所持专一详缓如此。初性甚急,后来养成至于是也。」
行夫问:「李先生谓:『常存此心,勿为事物所胜。』」先生答之云云。顷之,复曰:「李先生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者。古人云,终日无疾言遽色,他真个是如此。如寻常人去近处,必徐行;出远处,行必稍急。先生出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寻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声不加于前也。又如坐处壁间有字,某每常亦须起头一看。若先生则不然。方其坐时,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则必起就壁下视之。其不为事物所胜,大率若此。常闻先生后生时,极豪迈,一饮必数十杯。醉则好驰马,一骤三二十里不回。后来却收拾得恁地纯粹,所以难及。」
李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所居狭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渐长,逐间接起,又接起厅屋。亦有小书室,然甚齐整潇洒,安物皆有常处。其制行不异于人。亦常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居常无甚异同,颓如也。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
李延平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然又太和顺了。罗仲素衣服之类亦日有定程,如黄昏如何服,睡复易。然太执。
李先生好看论语,自明而已。谓孟子早是说得好了,使人爱看了也。其居在山间,亦殊无文字看读辨正,更爱看春秋左氏。初学于仲素,只看经。后侯师圣来沙县,罗邀之至,问:「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见曲折,故始看左氏。」
或问:「近见廖子晦言,今年见先生,问延平先生『静坐』之说,先生颇不以为然,不知如何?」曰:「这事难说。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尝见李先生说:『旧见罗先生说春秋,颇觉不甚好。不知到罗浮静极后,又理会得如何。』是时罗已死。某心常疑之。以今观之,是如此。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迭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下愈明静矣。」
旧见李先生云:「初问罗先生学春秋,觉说得自好。后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说有未安处。」又云:「不知后来到罗浮山中静极后,见得又如何?」某颇疑此说,以为春秋与「静」字不相干,何故须是静处方得工夫长进?后来方觉得这话好。盖义理自有着力看不出处。然此亦是后面事,初间亦须用力去理会,始得。若只靠着静后听他自长进,便却不得。然为学自有许多阶级,不可不知也。如某许多文字,便觉得有个吃力处,尚有这些病在。若还更得数年,不知又如何。
李先生云:「看圣贤言语,但一踔看过,便见道理者,却是真意思。纔着心去看,便蹉过了多。」
正蒙知言之类,学者更须被他汩没。李先生极不要人传写文字及看此等。旧尝看正蒙,李甚不许。然李终是短于辨论邪正,盖皆不可无也。无之,即是少博学详说工夫也。
李先生云:「横渠说,不须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费力。」
李问陈几叟借得文定传本,用薄纸真谨写一部。易传亦然。
李先生云:「书不要点,看得更好。」
李先生说一步是一步。如说「仁者其言也讱」,某当时为之语云,「圣人如天覆万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广说。须穷『其言也讱』前头如何,要得一进步处。」
李先生不要人强行,须有见得处方行,所谓洒然处。然犹有偏在。洒落而行,固好。未到洒落处,不成不行!亦须按本行之,待其着察。
李先生当时说学,已有许多意思。只为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
李先生说:「人心中大段恶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计利害、乍往乍来底念虑,相续不断,难为驱除。」今看得来,是如此。
李先生尝云:「人之念虑,若是于显然过恶萌动,此却易见易除。却怕于相似闲底事爆起来,缠绕思念将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来亦是如此。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变』。『改过迁善』,由此可至『所过者化』。」李先生说。
李先生言:「事虽纷纷,须还我处置。」
李先生有为,只用蛊卦,但有决裂处。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窥得,然其得处便有病也。」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
或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这里,又差从释氏去。」
问:「延平欲于未发之前观其气象,此与杨氏体验于未发之前者,异同如何?」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着意看,便也是已发。」问:「此体验是着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观观之。」
再论李先生之学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慎所不睹,恐惧所不闻』,便自然常存。颜子非礼勿视听言动,正是如此。」
胡氏门人
张敬夫
近日南轩书来,不曾见说尝读某书,有何新得。今又与伯恭相聚,往往打入多中去也。
钦夫见识极高,却不耐事;伯恭学耐事,却有病。
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南轩疏略从高处去,伯恭疏略从卑处去。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是两件事。如云:「仁义道德与度数刑政,介然为两涂,不可相通。」他在时不曾见与某说。他死后,诸门人弟子此等议论方渐渐说出来,乃云,皆原于伯恭也。
钦夫说得高了,故先生只要得典实平易。
敬夫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纔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故他门人,敏底秪学得他说话,若资质不逮,依旧无着摸。某则性钝,说书极是辛苦,故寻常与人言,多不敢为高远之论。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尔。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学者于理有未至处,切不可轻易与之说。张敬夫为人明快,每与学者说话,一切倾倒说出。此非不可,但学者见未到这里,见他如此说,便不复致思,亦甚害事。某则不然。非是不与他说,盖不欲与学者以未至之理耳。枅。
南轩尝言,遁闷工夫好做。
南轩说「端倪」两字极好。此两字,却自人欲中生出来。人若无这些个秉彝,如何思量得要做好人!辉。
或问:「南轩云:『行之至,则知益明;知既明,则行益』此意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学者工夫当并进,不可推泥牵连,下梢成两下担阁。然二者都要用工,则成就时二者自相资益矣。」
王壬问:「南轩类聚言仁处,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则气象促迫,不好。圣人说仁处固是紧要,不成不说仁处皆无用!亦须是从近看将去,优柔玩味,久之自有一个会处,方是工夫。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圣人须说『博学』,如何不教人便从慎独处做?须是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始得。」
问:「先生旧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出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辨此。」
问:「南轩与先生书,说『性善』者叹美之辞,如何?」曰:「不必如此说。善只是自然纯粹之理。今人多以善与恶对说,便不是。大凡人何尝不愿为好人,而怕恶人!」辉。
问:「南轩谓『动中见静,方识此心』。如何是『动中见静』?」曰:「『动中见静』,便是程子所说『艮止』之意。释氏便言『定』,圣人只言『止』。寓录云:「此段文已详了」。敬夫却要将这个为『见天地之心』。复是静中见动,他又要动中见静,却倒说了。」
问:「曾看南轩论语否?」曰:「虽尝略看,未之熟也。」曰:「南轩后来只修得此书。如孟子,竟无工夫改。」
南轩论语初成书时,先见后十篇,一切写去与他说。后见前十篇,又写去。后得书来,谓说得是,都改了。孟子说,不曾商量。
问:「南轩解『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将孟子『惠而不知为政』,立两壁辨论,非特于本旨为赘,且使学者又生出一事。」曰:「钦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如论语旧说,某与议论修来,多是此类。且如他向解颜渊『克己复礼』处,须说要先格物,然后克己。某与说,克己一事,自始学至成德,若未至『从心所欲,不踰矩』、『从容中道』时,皆要克,岂可与如此说定?因作一戏语云:『譬如对先生长者听其格言至论,却嫌他说得未尽;云,我更与他添些令尽。』彼当时闻此语,即相从,除却先要格物一段。不意今又添出『自始学至成德皆要克』一段。此是某攻他病底药,病去,则药自不用可也。今又更留取药在,却是去得一病,又留取一病在。又如『述而不作』处,他元说先云:『彼老彭者何人哉?而反使吾夫子想象慕用!』某与说,此譬如吾夫子前面致恭尽礼于人,而吾辈乃奋怒攘臂于其后!他闻说即改,此类甚众。若孟子,则未经修,为人传去印了,彼亦自悔。出仕后不曾看得文字,未及修孟子而卒。盖其间有大段害事者:如论性善处,却着一片说入太极来,此类颇多。」大雅云:「此书却好把与一般颓阘者看,以作其喜学之意。」曰:「此亦吕伯恭教人看上蔡语录之意。但既与他看了,候他稍知趋向,便与医了,则得。」
「南轩语孟子,尝说他这文字不好看。盖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字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要之,经之于理,亦犹传之于经。传,所以解经也,既通其经,则传亦可无;经,所以明理也,若晓得理,则经虽无,亦可。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他禅家尽见得这样,只是他又忒无注解。」问:「陆氏之学,恐将来亦无注解去。」曰:「他本只是禅。」干问:「尝看文字,多是虚字上无紧要处最有道理。若做文粗疏粗解,这般意思,却恐都不见了。」曰:「然。且如今说『秉彝』,这个道理却在『彝』字上『秉』字下。所以庄子谓『批大郄,导大窾』,便是道理都在空处。如易中说『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通便是空处。行得去,便是通;会,便是四边合凑来处。」问:「庄子云:『闻解牛,得养生。』如何可以养生?」曰:「只是顺他道理去,不假思虑,不去伤着它,便可以养生。」又曰:「不见全牛,只是见得骨骼自开。」问:「庄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见得个道理如此。」问:「他本是绝灭道理,如何有所见?」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见得如此。」因叹曰:「天下道理,各见得恁地,剖析开去,多少快活!若只鹘突在里,是自欺而已!」又问:「老子云『三十幅共一毂,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谓与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这里。」
林艾轩在行在,一日访南轩,曰:「程先生语录,某却看得;易传,看不得。」南轩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数,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轩曰:「孔子说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如以象言,则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圣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
龙泉簿范伯崇寄书来云:「今日气象,官无大小,皆难于有为。盖通身是病,无下药处耳。安得大贤君子,正其根本,使万目具举,吾民得乐其生耶!严陵之政,远近能言之。盖恻隐之心发于诚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
「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轩来。某亦赴召至行在,语南轩云:『汤进之不去,事不可为。莫担负了他底,至于败事!』某待得见魏公时,亲与之说。度住不得,一二日去矣。及魏公来,汤左相,张右相,都不可商量事。同进同退,独与上商量又不得。上又要商量,但时召南轩入,往来传言,与魏公商量。召南轩,上在一幄中,外无一人,说话甚款。南轩开陈临安不可居,乞且移跸建康,然宫禁左右且少带人,又百司之类,亦且带紧要底去。上曰:『朕独行,后妃宫禁之类,全不带一人去。临安淫侈之甚,如何居!』南轩祝上未须与人说,相将又诌。上曰:『朕不言。卿不须漏泄。』上因曰:『待朕取一文字与卿看。』上顾左右无人使,遂曰:『卿且待。』上自起去取。南轩见幄外皆是宫人,深惧所言皆为彼闻之矣。少顷上来,忘其文字。其后与宰相议用兵事,汤固力争。上曰:『朕旦夕亲往建康。』未几,外面哄哄地,谓上往建康。南轩见上问云:『陛下尝祝臣勿言。闻陛下对宰执言之,何也?』上曰:『被他挠人,故以此激之。』意思如此,记不全。南轩出入甚亲密,满朝忌之。一日,往见周葵,政府诸人在,次第逐报南轩来。周指之曰:『吾辈进退,皆在此郎之手。』是时南轩少年,又处得地位不是,而人情皆如此,何以成得事?南轩亦间至太上处理会事之类,太上曰:『尚记得卿父娶时如何事,卿今如此。』南轩奏边事并不可和之意,太上亦顺应之。临辞去,乃曰:『与卿父说,不如和好。』汤在相位时,有御札出来骂,亦有『秦桧不如』之语。然竟用之,不可晓,恐是太上意。上因广西买马事之类,甚向南轩,诸公已忌之。后到荆南,赵雄事事沮之,不可为矣。」先生又言:「近有谁说,在荆南时,司天奏相星在楚地,甚明。上曰:『张栻当之。』人愈忌之。」
南轩再召时,论今日自是当理会恢复。然不如此理会,须是云云,有札子。上大喜,次日降出札子,御批:「恢复须是如此理会。」即除侍讲,云:「且得直宿时与卿说话。」虞允文赵雄之徒不喜,遂沮抑。
南轩自魏公有事后,在家凡出入人事之类,必以两轿同其弟出入。
议南轩祭礼,曰:「钦夫信忒猛,又学胡氏云云,有一般没人情底学问。尝谓钦夫曰:『改过不吝,从善如流,固好。然于事上也略审覆行,亦何害?』」南轩只以魏公继室配,又以时祭废俗祭,某屡言之。
因说南轩为人作文序,曰:「钦夫无文字不做序。」
南轩从善之亟。先生尝与闲坐立,所见什物之类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齐整处,先生谩言之;虽夜后,亦实时今人移正之。
「春风骀荡家家到,天理流行事事清。」此南轩题桃符云尔,择之议之。
钦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资;善人,不善人之师。』与孔子『见贤思齐,见不贤内省』之意不同。」为老子不合有资之之意,不善也。